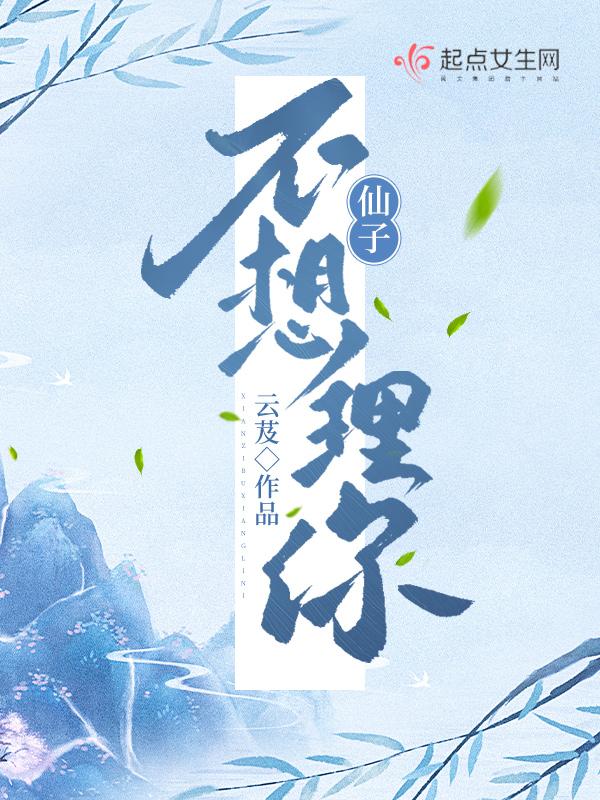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禁止碰瓷笔趣阁 > 第106章(第1页)
第106章(第1页)
许映白调了下水温,热气再次翻涌:“如果买错城市了,怎么办呢?”
“再买回来呀。”谢乘风说,“我要来这里,不去别的地方。”
心脏抽痛的感觉蚕食着许映白的神经,他用指腹点了下谢乘风的眉梢,嗯一声,又吻下去。
谢乘风闭上眼,忽而又睁开,入目看到许映白漆黑眼睫,细看还有一丝颤抖,有限的视野里他只能看到许映白模糊的侧脸,宁静温和,独有一种精雕细琢的温润。
湿润温暖的口腔将他推到另外一种的渴望里,谢乘风身上未着寸缕,转念一想,还是那句老话,人都到手里了,还怕什么。
于是,他伸手探下去,轻轻勾开许映白的裤子拉链,停了一秒,还是先将许映白的上衣给胡乱地脱了。
温暖的肌肤贴上来时谢乘风仰头深吸了一口气,等摸够了许映白的身体,他继续刚才未完成的动作。
当谢乘风的手落在小腹,往下挪的那一秒,许映白抬身,抓住他的手又按在了墙壁上。
谢乘风不解,问他:“不要吗?”
以往滚在一张床上,每次想要再进一步时谢乘风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抵抗,许映白以前不知,现在却已然明白,那一丝抵抗里有对他不相识的委屈,也有怕他误会的担忧。
许映白放开他的手,摸到自己裤兜里:“现在肯了?”
“你要是不想我们还继续那样。”谢乘风挑挑眉梢,还在气他,说罢放下手往许映白身下蹭了两把,“我们也练过几次了,我技术好多了。”
许映白极轻地笑了声,抓起他的手放在唇边吻了吻。
忽而一声叹息,让谢乘风笑意凝固住,紧接着水声停止,一件柔软的浴袍被裹在身上。
许映白将他抱到外面的洗漱台上,站在他两腿中间静静注视着他,谢乘风疑惑之际察觉手掌被掰开,随即手心一凉,他低头一看,带有许映白首字母暗纹的那面映入他的眼底。
谢乘风攥住,背脊瞬间僵硬。
许映白抬起他的脸,低声问他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一句跟当年同样的问话,让二人瞬间回到那间装潢陈旧的便捷旅馆。
由于旅馆位置较为偏僻,设施属实算不上优良,或许是为了省电,走廊里的灯光调的很暗,甚至在楼梯处散着几张超市打折的广告宣传单。
一间双人房,潮湿闷热,空调开了好半天,才缓缓听见嗡嗡运作声,隔壁深夜不睡,开着电视,透过不甚隔音的墙壁闷闷的传过来,细细一听,竟放的还是一部鬼片。
许映白身上挂着包,歪在床上一动不动,偶尔呼吸声沉一下,告诉另外一人他还活着。
谢乘风把吉他放好,过去踢了踢他的脚尖:“诶,醒醒。”
许映白眼皮动了下,翻身躺的更平稳了。
周遭暂时没有响动,唯余恐怖的音效忽轻忽重地传来,不知多久过去,许映白感觉有人勒自己,迷迷糊糊睁开眼,看见眼前有一团模糊的影子。
“干什么?”许映白语气正常的不像是醉酒,“动我衣服干什么?”
谢乘风半跪在床边,手里拽着许映白的包带,闻言拧了下眉,烦到不行的样子:“谁他妈动你了,我好心好意给你把包摘了。”
许映白顺着他的手看过去,只见一截青色血管沿臂侧攀延上去,他忽然好奇,伸出自己的胳膊比了比,比了半晌,也没看清到底谁的更有力量些。
等谢乘风帮他把包从身上摘下,许映白闭着眼扯下t恤,腰带一解,往地下一扔,扭头问他:“刚刚你是不是挨打了?”
谢乘风躺在另外一床,看他一眼说他多管闲事。
彼时许映白刚参加完林汀的庆功宴,被人好好算计了一把,对多管闲事四字尤为敏感,他慢吞吞地坐起来,又把衣服穿上,拎起包就要往外走。
谢乘风看着他这一套动作,等他打开门的时候,叫了一声:“许映白。”
“你认识我?”许映白停下,回头问他。
谢乘风忽然笑了,眉宇舒展的分外俊朗:“你这是喝了多少?”
“忘了。”许映白说,“在饭店喝完,我自己又出来喝,老板说要关门了我才走的。”
外面不知那间发出一声重重的响声,像是凳子倒地的声音,许映白开门看一眼,扭头对他又说:“这么吵。”
“不想住可以出去。”谢乘风枕住双臂,嘴下对他恐吓,“外面下雨呢,现在出去你死外面都没人知道。”
许映白拍了下房门,关上又坐回来:“我才不死。”
谢乘风转了个身,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望他,似是引诱:“我是你救命恩人,你不感谢感谢我吗?”
许映白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一下,几分钟后,谢乘风误以为他坐着睡着了,他才出声说:“你脾气有点大。”
谢乘风一梗,腿上挨的那下莫名隐隐作痛。
“刚那个人是不是揍你了?我看见了,你怎么不躲呢?”许映白说,“打不过就跑,跑了又不丢人,你傻站着干嘛?”
谢乘风反驳:“跑了怎么不丢人?被人知道不得笑话死我?”
“你的生活是给别人看的吗?”
轻轻一句话,一股清明之感荡入心间,谢乘风张了张嘴,竟无法辩驳。
他理解的生活绝不可以低头,更不可以退缩,以为这样便能被人高看一等,岂料原来他一直在固步自封,以为的那些似乎没有人在乎。
他的生活只是他的生活。
“我从小到大成绩很好,长大了也没怎么折腾过,但是不管再怎么听话的孩子,总归有那么一阵儿讨人嫌的时候。”许映白把腿放在床上,似是喃喃自语,“我青春期就挺叛逆的,爸妈不让干什么专门干什么,把他们气的不行,最严重的一次是我跟他们出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