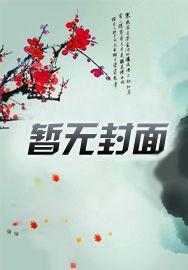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爆炒挑食小少爷免费 > 第229章(第1页)
第229章(第1页)
史如意轻咳一声,掩去嘴角的笑容,好歹要给自家师傅留点面子。
梁婆婆探头过来看几眼,「让我老婆子先瞧瞧,哟,酥脆合宜,饼身金黄如鳞片,二月食之,百病惧龙体外跑,故起名为』龙鳞饼『——了不得,真是好俊的名!」
梁翁对梁婆婆敢怒不敢言,只得借着点心名册的由头撒气,「山药与板栗各切成片,加羊汁,煮熟至酥烂成羹。因盛在碗中,黄白两色交相辉映,又取名为』金玉羹『。」
他眯眼读到这里,眉头皱得更紧,负手道:「这不就我教你的那道山药板栗糕麽?好好的,取这般花里胡哨的名作甚。」
史如意还没说话,梁婆婆先急得跺脚,「害,你这老头子,每日净晓得钻厨房了,对外头经营买卖之事真是一概不通。」
「起个好听名,你晓得能省多少口舌事?便如相看人家郎君,未得见人,先叫大名来听听,若是起得有水准,心下便先爱了三分,知晓人家底蕴丰厚,不是那等粗俗大汉可比的。」
史如意听得猛猛点头,连声赞道:「婆婆说的正是!」
梁翁被她们俩噎了一下,又板起脸道:「都是花架子,有没有真本事,一尝味道就知。」
史如意笑眯眯的,赶忙在这边也顺毛捋几下,「名呢,是负责吸引新客的;味呢,是负责留住熟客的。二者缺一不可,尽善尽美,做生意才能长久。」
梁翁从鼻孔里「哼」一声,这才不情不愿承认,「也有两分理,只是为何把做法也写得那麽详尽?」
这算问到点子上了,史如意忙正襟危坐,清清嗓子,把将来开分店丶训练厨子的想法拣着重点交代了。
「两家分店开业,如今人手断然不够,招新厨子前把方子总结出来,也是为了方便後头统一口味,以免出现客人出了东家铺子,隔几日心心念念,到西家来尝,却发现味道远逊於之前的情况。」
此时难出现後世之类的连锁店,史如意琢磨着,除去路程遥远,大部分人都留恋*故土人情,不愿离乡以外。从事庖厨一途者又多为市井小民,大字不识一二,做吃食全靠「玄学经验」。
分身乏术,子承父业却技艺不精,以致门店没落的情况屡见不鲜。
史如意心头觉得惋惜,从古到今,有多少美食记载在诗词中被人传颂,其技艺做法却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之中,让人只能遥想其美味。
梁翁一听,越发拧起眉头,嗤她异想天开,「原料大小不一,切片厚薄不一,要蒸煮烤制时间也因之不同,做起来全靠日常功夫经验,哪是这麽几句便能概括完全的?」
「说的这麽简单,要是人人看着方子就能做得出来,咱家这铺子也不用开了。」
史如意志向不小,但梁翁总心有顾虑,当年再辛苦,他和老婆子也把「祥和斋」的名声守了几十年。
能把分店开到大江南北固然是好事,光是听着都让人心潮澎湃,但若是砸了自个儿招牌,还不如就这般守着老铺子过。
史如意早料到梁翁会这般说,胸有成竹笑道:「若像师傅当年带我那样,从头到尾,手把手教出来,还不知要费几年的功夫……但如果细细分工下来,揉面团发酵由一批人,装饰花样是一批人,蒸调烤制又是另一批人,要学的东西少了,见成果也快。」
这个模式若是管用,史如意打算将来在酒楼食肆中也有样学样。
至於管事和跑堂,梅师傅带的安阳女子学堂里便有现成的好人选,授学多年,先生学生彼此都知根知底,人品能力一问便知。
这个年代,小娘子要自食其力,在外寻到活计养活自己,总有这样那样诸多不易,史如意盼望着自个儿酒楼开大做大,也有「达则兼济天下」这层意愿在。
她嗓音不疾不徐,自带着一股溪水般安抚人心的力量,就连凭空画出的大饼也让人信服。
梁翁紧皱的眉头慢慢松开,若有所思。
梁婆婆更是直接拍手叫好,「老头子,我看小如意这个点子要得!每个厨子只学自己手头半截,便是回头泄露到对家去也不怕。」
在两人灼灼目光注视下,梁翁摸摸鼻子,到底露出一点笑容来,咳嗽两声道:「算了丶算了——我一个老头子懂什麽,反正这铺子交给你跟罗儿,你们年轻小娘子,爱怎麽折腾就怎麽折腾去罢!」
话是这麽说,梁翁眼里也不由得透出几分自豪来,看到後继有人,他哪怕是现在闭眼都觉欣慰。
人老了越是不能闲下来,心头要有事惦念着丶忙碌着,身子骨才能硬朗。
史如意心头一咯噔,忙伸手抓住梁翁的衣袖,故意不依道:「好哇,被我发现了罢,师傅你想偷懒可不行!要说这做点心手艺还属师傅功力深厚,徒儿最多学到九牛一毛……我看呐,这《花点经》还是拜托师傅来写才好!」
梁婆婆也做出严肃神情,「如意你放心,从今个儿起我督着老头子写,每日写不完一篇,不让他上榻睡觉。」
梁翁瞪她们一眼,半晌,自个儿也忍不住笑了。
第124章藤萝饼
史如意来祥和斋里,从没有一回是空着手走的。
梁婆婆和梁翁待她如待罗娘子一般,平日里见着什麽吃的玩的,自个儿总舍不得用,只好好地收在柜里,等史如意从京城回来。
「还有这盒子藤萝饼——也是你师傅亲手做的!如意你带回去,跟你娘一块儿吃。」梁婆婆将最後一个沉重的竹盒塞到她手里,环顾一圈确保没有遗漏,这才满意地点点头。<="<hr>
哦豁,小夥伴们如果觉得不错,记得收藏网址或推荐给朋友哦~拜托啦(>。<)
<span>:|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