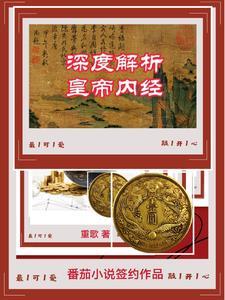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百花深处剧情分集介绍 > 第53节(第3页)
第53节(第3页)
终于,在一家热闹的面馆里,她看到花儿面前放着一个空碗和一壶茶水。叶华裳的心快乐得要飞起来,但她按捺住激动,提起裙摆缓缓走过去,假意在店里巡视一圈,用为自己选座的模样,最终坐到了花儿面前。
见花儿漾起笑脸,忙伸出手指比了个“嘘”,叫了两碗面,她自己一碗,又大声道:“占你的桌,送你碗面。”
面馆嘈杂,无人注意她们,面端上来叶华裳推一碗给她:“吃吧,多吃。”
“叶小姐,你可还好?”花儿忍不住小声问她。
“很好,恶名在外的阿勒楚的妻子,无人敢惹,怎么会不好?”
她这样说,花儿就知晓她过得不好。她有点难过,想对她说你走后二爷惦记你,夜不能寐。后一想,此刻说这些,犹如在叶华裳的心头扎一把刀。
叶华裳却主动问起:“他怎么样?”
“他回京城了。在燕琢城破前将家产都挪到了京城。”
“你呢?”
她们眼下应当各有立场,但花儿不想欺骗叶华裳,她已经够可怜了,若再被她欺骗,岂不是更可怜?于是对她说:“我家人都死了,我去参军了。如今我是谷家军的斥候。”
叶华裳闻言抬起头看她,在她的印象中,那个“小书童”好生机灵可爱,却也瘦小羸弱,如今却成为一名战士。“小书童”比她的脊梁要硬。
花儿吃了口面,对叶华裳说:“原本是来采办,适才见到您就想与您说说话。也不知为什么。”
“我每两月来一次良清,若你愿意,下次也可找我说话。我平日里也不知该与谁说话,额远河那边只有草场和牛羊,还有我听不懂的鞑靼话。”叶华裳对花儿说:“你不恨我吗?鞑靼屠了燕琢城,而我现在…”
“我恨你做什么?你自己又不愿意!我只心疼你,一个人孤苦伶仃。至少我还与自己人在一起,难过时有人讲话、无助时有人相助,而你…”
叶华裳闻言笑了笑,轻声道:“有人举刀为民,有人委身为民,女子的家国天下,不必拘泥于眼前。”
“向前看。”她说:“向前看,向远看。”
尽管她是别人眼中的“弱质女流”,是阿勒楚的“玩物妻子”,是随时要被送出的“牲畜”,叶华裳也曾恍惚以为她是,但当她站在额远河边,想起燕琢城那些美丽的春日之时,她知晓:她不是。
她不是,亦不想用言语为自己申辩,世人如何看她,于她而言并不重要。女子立身于天下,不立身于别人的言语中。
她见到了花儿,知晓她从军了,就知晓虽然她们踏上殊途,但一定会同归。
“你今晚宿在良清吗?”叶华裳问她。
“此刻已然不合适上山了。”
“你宿在行宫边上的那家小客栈里,我能照应你一些。”叶华裳道。
“多谢叶小姐。”
吃过面,叶华裳起身离去之前突然问道:“白二爷可有心上人了?”
花儿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,叶华裳也不等她答案,转身走了。花儿片刻后出了面前,她在前面走走停停,她在后头走走停停。二人都做出闲逛的样子,无非是想在故人的目光中多待片刻。
当叶华裳举起一个小花簪比到头上时,就恍惚觉得她还是当日那个燕琢城里好看的奇女子。良清的夏风吹着她的裙摆,简直是无法言说的美丽。花儿又想起当初和白栖岭十里又十里送她,恍惚就在昨日。她甚至能在只言片语中体察到叶华裳的痛苦。
夜晚的良清城令花儿恍惚。
上一次的惊心动魄犹在记忆之中,这一次的安宁也令人毛骨悚然。所谓的“行宫”门口点着火红的灯笼,花儿探出头去一直看着。
她这间小屋子只容纳一张床,几步就可到窗边。天一黑街上就没有人,再过一些时候,不知从哪冒出了许多人高马大的鞑靼。他们走进酒馆、饭庄,开始饮酒打闹。这显然是良清城的常态了。
花儿关上窗,拿出白栖岭的信翻看。她有些懊恼,原本有机会将她和白栖岭的事告诉叶华裳,错过那个说话的机会看起来就带着有意欺骗。
行宫方向有了响动,花儿探出头去,那一幕令她震惊。她看到一个女子叩响了行宫的门,那女子她认得,是她有几面之缘的铃铛。她记得白栖岭切人手指时她迅速关上门、记得她走在无人的街乡塞给她一个馒头。
read_xia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