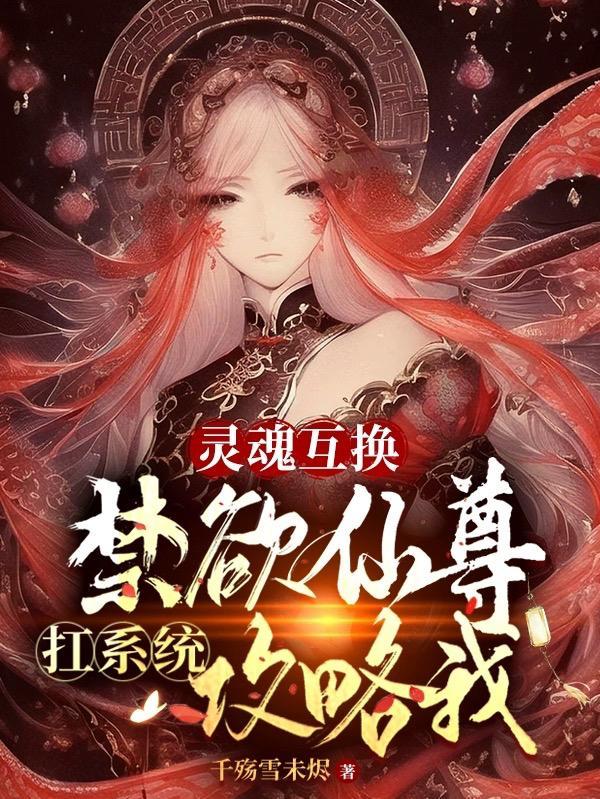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捡来的皇子夫君 > 第7章(第1页)
第7章(第1页)
“上供的人都有谁?说清楚。”沈缇意蓦地抓住话中的关键。
“上达湘楚知府,下至乡里财主。”回话的人牙子还颇得意,他眼珠一转,特意点出这行当攀上的权贵不好招惹。
他相信,沈缇意一行人听闻买家的名头想必不会再插手此事,这一桩买卖可不是几个路见不平的莽夫能管得了的。
“湘楚知府”沈缇意眉心一蹙,骤然握紧了拳,倏地砸向长桌,盛怒道,“湘楚灾情一拖再拖,位居知府竟然还有余力沉溺女色辱没人妇,他将黎民百姓置于何地,又将大梁置于何地!”
就在此时,远处渐渐传来走动声响,来人行进速度极快,刀刃与冷甲相撞,声势骇人。
不久,一支兵卒停在门外,打头的正是领命带人从客舍赶来的乌桁。
“公主,背城军已就位。”为协助赈灾,梁元帝特命原昭武将军袁奉先麾下、现归沈缇意统辖的队伍——背城军随沈缇意南下。
“将这些人悉数绑了,今后我倒要看看,赈灾无力的知府大人能给我什么说法。”
乌桁应下,候在门外的兵士应声而动,将屋内的贼人押走。
人牙子一听“公主”名号,才知此番是大难临头,绝无回旋余地,方才高涨的气焰骤然偃旗息鼓,一个个如丧考妣,哭天抢地似的叫屈。
祝续玖眼看沈缇意大步走出房外,鬼使神差跟了上去。
方才见她气势不凡,又见她调度有方,已猜到她大有来头,没料到救命恩人竟是当朝公主。
大梁只有一位公主,那她自然是那位戍边有功而声名远扬的长公主了。
祝续玖心绪震动之下,跟在这位皇女身后竟怀着些少有的激动,在她看过来时甚至不知所措起来。
这位公主比他还小一些,已经是护国立功的女郎了。
幸亏适才他一直留心这位长公主的所言所行,终于找回自己的思绪:“公主,可是为了湘楚大旱一事而来?”
他从善如流地改了称呼,“我半月前便来到此地,方才草民多有不敬,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,草民一定尽数相告。”
“此地名为邵州,位处湘中,乃是旱情频发之地。邵州知州名叫卫辽,数日前因监守自盗被湘楚知府魏礼群上折弹劾,丢了头上的乌纱帽。”
“上折弹劾?”沈缇意把这四个字咀嚼了一遍,还有谁能比那湘楚知府更放肆么。
“公主,罪名存在与否从来不在其行径,而在服众。从卫辽家中搜出的赈银铁证如山,当前饿殍盈野,死者枕藉[壹]。任他有三寸不烂之舌也无从辩驳。”
沈缇意微仰起头,看了一眼比她高出半个头的青年。
祝续玖明明说的是他人之事,眼神却找不到落点,他瞧着虚空,就好像透过卫辽的际遇想到了什么人。
“这么说,祝行俭,莫非你知道个中原委?”沈缇意的脚步倏忽停下来,落后她半步的祝续玖也跟着一停,正好与她并肩而立。
“草民即使知晓内幕,也无从下手。公主既要寻根究底,遭遇这场飞来横祸的卫大人必定感激不尽。”祝续玖躬身作了一揖,便将来龙去脉细细道来。
原来,卫辽在邵州就任知州已有五年之久,坊间风评一向颇好,不过此次风波牵扯到赈银去向,大灾中积压的民愤便朝卫辽倾泻而下,湘楚知府魏礼群的目的,就是要利用民心所向,把卫辽拉下高台。
“当日一名自称卫辽家仆的男子向魏礼群告发,魏礼群即刻命人到卫辽府上搜查,果然在那仆从指认之处搜出了赈银五百两,随后卫辽即被撤职,搬离知州府。”祝续玖道。
沈缇意:“那仆从姓甚名谁可有眉目?”
“这人在告发魏礼群后就销声匿迹了,名姓倒是清楚,姓岑、单名一个‘鸣’字。”
沈缇意一扬眉,“有名有姓,自然好办,”她亲自领了一小队人马,当即赶往知州府。
只要这个人有存在过的痕迹,她就势必要查清楚。
能让知府如此大费周章的人物——或许,卫辽就是突破赈灾困境的关键。
祝续玖紧随其后。
“公主,府上家仆籍贯、变动都记在此名册。”
知州府上的管事亲自将沈缇意迎进府中,拿出一本簿册,很薄,不过尾指一个关节宽窄。
“管事的,你可有在府上听过‘岑鸣’这个人?”沈缇意接过名册,一面翻看,一面发问。
“府上照顾知州起居的下人就那么几个,小的都眼熟,能发现知州藏匿私银这等秘事的,应是极亲近之人,告发知州的岑鸣,既不知来历,也不知去处,只怕是别有用心。”
“如此,便无需再查。”几句话的功夫,沈缇意已然翻阅了一遍名册,便递还回去,“管事,你家主子现下在何处,带我去见见。”
“知州大人正宿在小人家中,我得他一手提携,卫大人一日不能沉冤,小人便一日不敢忘恩负义。”管事心中不甘,见今日来了这样一号大人物,哪里会放过护主的机会。
“你倒是个重情义的,”沈缇意一哂道,“若卫辽当真清白,我自会还他公道,若是弄虚作假,在我这说破嘴皮子也行不通。”
管事虽然有些摸不清沈缇意的意思,但听了这话明白自己求情也是无用功,只垂首应下,不再多言,径直领着沈缇意一行人去寻卫辽。
“这位公主果真是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性情,一家之言在她面前是没有用的,”祝续玖心道。
他跟在兵马近旁,远远瞧着沈缇意的背影,正在思考毛遂自荐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