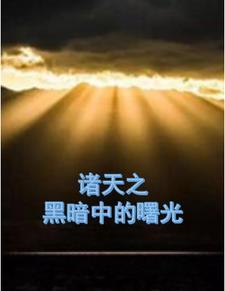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瘫痪的弟弟 > 第48章(第1页)
第48章(第1页)
可那冰冷的现实却如同一座无法撼动的大山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心痛
段舒禾独自躺在昏暗的病里,四周静谧得可怕,只有墙上的时钟发出单调的滴答声。
但这种平静只是表象,每当他合上双眼,可怕的梦魇便如汹涌的潮水般将他淹没。
在梦里,那车祸的场景如同被诅咒的影片不断回放。
他看到那辆汽车如失控的猛兽般朝他冲来,刺眼的车灯像是撒旦的眼睛,瞬间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。
巨大的撞击声震耳欲聋,金属在扭曲、玻璃在破碎,每一个声音都像锋利的刀刃,狠狠地刺进他的灵魂。
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车内被甩来甩去,骨头与座椅、车门碰撞的剧痛清晰可感,仿佛那不是梦,而是真实发生的二次伤害。
每次从这样的噩梦中惊醒,段舒禾都大汗淋漓,病号服紧紧地贴在背上。
段舒禾呼吸急促而紊乱,仿佛刚刚从生死边缘挣扎出来。
黑暗中,他瞪大双眼,眼中满是惊恐和无助,那梦魇中的画面在眼前挥之不去,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,不断地冲击着他脆弱的神经。
段舒禾虽从车祸的重创中渐渐恢复,身体在好转,可心灵仿佛仍被困在那恐怖瞬间的阴影里。
每当父母来送饭,段舒禾只强提精神应付一两句,便眼神空洞地望着餐盘,饭菜散发的香气无法勾起他丝毫食欲。
每一口食物对他来说都像是负担,他坐在餐桌前,看着满桌精心准备的饭菜,却感觉不到丝毫的诱惑,食物散发的香气在他的鼻腔里变得刺鼻,每一次试图把食物送入口中,都会引起他强烈的反感。
他觉得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,食物在嘴里变得如同嚼蜡,难以下咽。
他的眉间总是深锁着,像是有解不开的结,周围的欢声笑语在他耳中宛如隔世,他被自己的心结紧紧缠绕,挣脱不得。
渐渐地,段舒禾对进食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抗拒。
每一顿饭都成了一种煎熬,他吃得越来越少,身体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。
原本合身的衬衫变得宽松,裤子需要系上更紧的皮带才能勉强挂在腰间。
脸颊凹陷下去,颧骨突出,皮肤失去了光泽,变得苍白而松弛。每一根骨头都在消瘦的身体上凸显出来。月余,他竟瘦了30斤,整个人看起来就像被抽干了生命力的躯壳。
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对他的变化忧心忡忡,纷纷前来劝慰。然而,他就像被一层无形的屏障隔绝在自己的世界里,对外界的关心置若罔闻。他听不进那些温暖的话语,也感受不到亲人们的担忧和爱意。
而夜晚的噩梦依旧如影随形,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从短暂的睡眠中拽出。
每一次惊醒,他都感觉自己的精神在崩溃的边缘又滑进了一步。
他开始害怕夜晚的到来,每一个黄昏都像是死亡的预告,让他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。
他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摆脱噩梦,比如睡前喝热牛奶、听舒缓的音乐,但这些都无济于事,那梦魇就像扎根在他灵魂深处的毒瘤,无法消除。
在这个恶性循环中,段舒禾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陷入了极度糟糕的境地。
直到许奕珩从那个令他厌恶的小后妈那里偶然得知段舒禾的状况。
此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在他心头炸响,他的眼中瞬间闪过慌乱与担忧,再也顾不上正在进行的课程。
他匆匆收拾书包,在老师和同学惊愕的目光中夺门而出。
许奕珩脚步急促而凌乱,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,仿佛要冲出嗓子眼儿。
校园里的风景在他眼中如浮光掠影般掠过,他满脑都是段舒禾那虚弱消瘦的模样。
当他赶到段舒禾所在之处,在门口停住脚步,大口喘着气。
许奕珩几乎是冲进病房,那扇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合上,发出的声响在这紧张的氛围中显得格外突兀。
一进门,刺鼻的消毒水味道便直往鼻腔里钻,让他的呼吸猛地一滞,而各种医疗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交织在一起,如同催命的音符,一下下撞击着他的耳膜。
段舒禾安静地躺在那里,往日的风采早已消失不见。
此刻的段舒禾像是一朵曾经娇艳盛开在春日暖阳下的花朵,却不幸遭遇了狂风暴雨的肆虐。
如今正摇摇欲坠、濒临凋零。
段舒禾嘴唇干裂得厉害,泛着令人揪心的白色,刺痛着许奕珩的眼睛。
眉头微微皱着,那眉头间的褶皱里似乎藏着无数痛苦的梦魇,即便在昏睡中,也无法摆脱那如鬼魅般缠绕的折磨。
周围的仪器管子密密麻麻地连接在段舒禾身上,它们像是无数条冰冷无情的锁链,将段舒禾紧紧地束缚在这张病床上,让他无法逃脱。
许奕珩的脚步变得无比沉重,每向前踏出一步,都仿佛要耗尽他全身的力气。
双腿似乎被无形的力量拖拽着,可他的目光从未从段舒禾身上移开。
他一步一步缓缓地靠近病床,每一步都像是踏在自己的心尖上,那钻心的疼痛让他的眉头也不自觉地皱了起来。
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段舒禾,眼中满是心疼、担忧和藏不住的情意。
那情意如同燎原的星星之火,不断蔓延燃烧,却又被无尽的悲伤所笼罩。
许奕珩的手微微颤抖着,像是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树叶。
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,想要触碰段舒禾,想要确认眼前这令人心碎的场景是真实的,却又害怕自己粗糙的触碰会惊扰到段舒禾这难得的安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