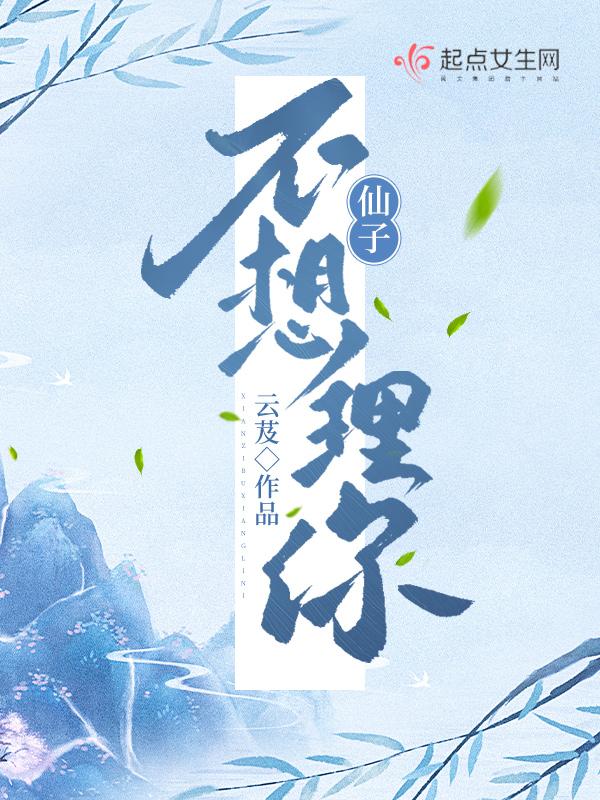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大司马宠妻日常免费 > 第107章(第1页)
第107章(第1页)
乐知许一惊,“有这等事?”
“可不是么,现在他人被关了起来,要不是恰巧我父亲有位门生——恰巧是当地校尉来访,无意中提到此事,我还被蒙在鼓里呢!”向昭君面色哀怨,“我说怎么最近一直没给我回信”
“新上任的太守”乐知许脑子飞快转动。
这新太守背后的人,恐怕就是要趁时彧昏迷之时,将玉人军逐渐控制或者瓦解,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,得赶紧通知他才行。
可她又想起他的话。
“不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,就风风火火赶来,你要相信我。”
难道,他装病,就是为了要引这些人出洞?
那也太冒险了些。
向昭君没发觉她陷入沉思,自顾自说着,“那校尉明日要回户县,我便跟他回去,若是能从中周旋一二,想办法叫他们把人先放出来,就再好不过了。知许,你在听么?”
“嗯?”乐知许回过神来,“阿姊,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了,京兆距离户县更近,说不定三叔母已经得了消息,正在想办法了。你这一路上,千万注意安全。”
“我会的,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向昭君攥起拳头,“等天下太平,我们再狠狠赚它一笔!”
皇帝一筹莫展。
之前两件皇弟毒杀案,摆明了是冲着时彧去的,他心里也清楚,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
他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思,静观其变,意图哪一方示弱时,再适时加以打压,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谁知事情竟急转直下,时彧重伤,皇后小产。
虽然之前太医令曾委婉表示过,皇后所怀龙胎,应该无法顺利降生,可真这么快就小产,皇帝还是有些意外的。
近几次去看皇后,她都哭哭啼啼,寻死觅活的模样,可面色又红润得简直不像话,甚至好像还丰腴了些。
他不得不仔细思索起,自皇后有孕起,前前后后的事来。
可还未等他想清楚个所以然来,大臣们便齐齐求见,各说各话,诉起自己的苦来。
为首的便是大司农田畚,说国库亏空得紧,已经开始拖欠征北军的粮饷了。
而北方军报,匈奴滋扰边境成性,征北军去打,他们便跑,从不恋战,使得征北军分身乏术,若再克扣军饷,恐怕战士们会丧失斗志,无力应对。
此言一出,少府也不干了,说几个月前以国库空虚为由,将山海池泽之税,纳入国库,宫内用度处处吃紧不说,如今国库竟依然亏空,非要田畚说清楚,钱都到哪里去了不可。
各州刺史也都纷纷上书,苦于受流寇所扰,想请朝廷派兵清剿。
就连钦天监也跟着凑热闹,说夜观天象,见文曲、玉衡、延年等星皆昏暗无光,乃是大凶之兆,恐生瘟疫。
皇帝被他们闹得,一个头两个大。
要知道,这些琐碎的事,一直都是时彧来处理,即便是有奏章递到他手里,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只要当时能含糊过去,过后时彧总会想法子处理掉的。
从清晨一直僵持到午膳时分,这才借口用膳,得一息空闲,谁知赵镇却掐着时间,不请自来。
他知道赵镇要说什么,皇后小产之事,还一直未有交代。
不是他不心疼自己的骨肉,皇后有孕,他也开心至极。只是皮之将存,毛将焉附,他不站稳脚跟,即便是生了儿子,又有何用,还不是同他一样,只能当个傀儡?
他没想到法子应对,可自从时彧出事,赵镇的态度也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强硬,还真不是他能推诿得了的。
“臣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啊?打扰陛下用膳了?”赵镇嘴上虽这么说着,可步子却没停,径直走到皇帝面前,微微行了个礼。
皇上笑道:“没有,朕也用完了,苏善。”
苏善忙给候着的宫人眼色,将食案撤了下去。
赵镇也不客气,自行在案前坐了下来,“陛下,臣着人问过了,皇后娘娘还是忧思过重,茶饭不思,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。”
“太尉不必忧心,朕已经叫太医令和太官令,时刻候在椒房殿了,定会好好照顾皇后的。”
“婉儿从小便要强,”赵镇神色不悦,改直呼皇后闺名,“这一回,对她身心打击可都不小,陛下想好如何处置时彧了吗?”
皇帝眼睛一眯,抬手抚了抚下颌,看来赵镇这是急于置时彧于死地啊!
若是赵家一家独大,将原本属于太尉的兵权收回,以赵镇和皇后的行事风格,他的日子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。
没有属于自己的兵权,再怎么折腾,也不过是把命运,送到另一个人手上拿捏而已。
想到这,皇帝面露难色道:“事情发生时,时卿正昏迷,真要论起来,顶多也就是个管教不利,去太尉府门前闹事的随从,杀了就杀了,若真拿此事追究时卿责任,恐怕难以服众啊?”
“陛下!”赵镇虎目一立,“婉儿腹中失去的,可是您的第一个孩子啊!若在此事上妥协,日后有心之人残害起皇嗣来,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?”
“太尉言重了,朕已经叫御史台的人,去查问了,去了几次,时卿也没醒,还是给他们点时间吧。”
“时间?”赵镇鼻子里哼了一声,“要臣提醒陛下,御史台手里,还攥着两件无头冤案吗?”
皇帝闷着不出声。
大殿里静得,只能听到两人浊重的喘息声,宫人们都恨不得把头埋在胸脯里,憋死在原地。
正焦灼之际,有宫人在殿门侧面探了头,苏善踮着小碎步过去,侧耳听完,回身大喜,禀告道:“陛下,司马大人醒了,司马大人醒了呀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