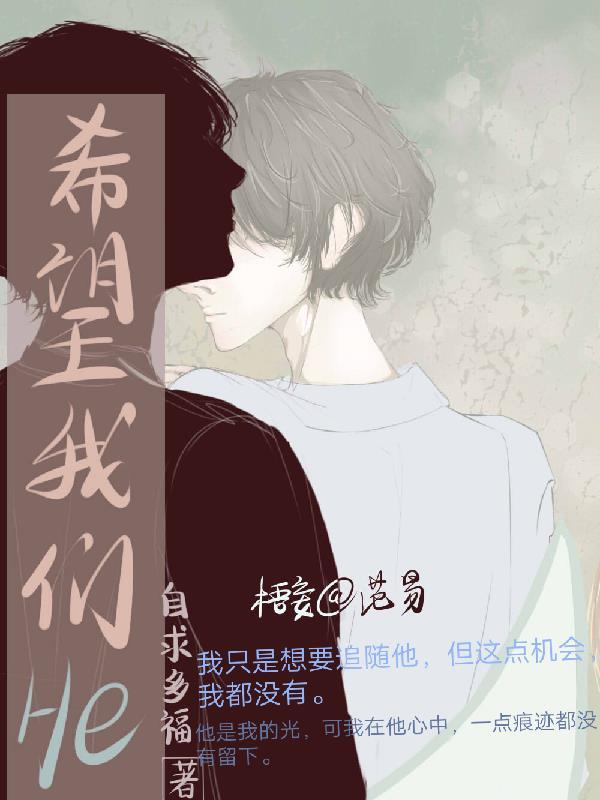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夏季雨完整版 > 第96章(第1页)
第96章(第1页)
“不用了,药店早关门了,我自己回家弄弄吧。”赵红梅温和的冲着林芳芳笑着。
“我给你弄吧,你这头上伤的……自己涂药特别不方便……”林芳芳坚持。
“那行吧,跟姐回家。”赵红梅斟酌了一下,爽快的对她说。
赵红梅骑着车,后面载着林芳芳,两人一车在林城的夜晚里无声的滑行而过。
车子停到了家属区的一栋红砖楼下,她俩锁好车,上了楼。
到了门口赵红梅停了下来,小声说“孩子睡觉呢,咱俩小点声。”
“好、好。”林芳芳连连答应。
和林芳芳家相比,赵红梅住的这间房子小小的,一室一厅,一览无余。
“你先坐会儿。”赵红梅悄声说着,转头不知道去忙了些啥。
林芳芳酒劲泛上来,又有点犯恶心,就去了厕所,用水抹了一把脸。
等她回客厅的时候,赵红梅已经坐在那等着她了,桌上还放着一个小碗,里面盛着一碗胖胖的汤圆。
赵红梅冲她微笑着:“吃点汤圆吧,一宿没吃东西,还吐了一厕所,吃点东西能好一点。”
她看向赵红梅,半天没出声。
“愣着干嘛?过来呀,专门给你煮的。”赵红梅小声说。
林芳芳一股鼻酸,赶紧坐了过去,拿起了勺子,吃了起来。
她确实饿坏了,软糯甜滋滋的白糖馅汤圆,一颗颗都是乖乖的,在乳白色的汤里浮起来。
一滴泪吧嗒滴到了碗里,她没在意。
赵红梅像亲姐姐一样爱惜的看着她。
吃完汤圆,林芳芳拿起蘸了碘酒的棉球,为赵红梅擦拭头上的伤口。
她的动作很轻柔,轻轻的吹气,生怕自己弄疼了赵红梅,手脚很利索,很快就做好了简单的消毒和包扎。
赵红梅看了看卧室里面,月光下,小小的赵越睡的很熟。
她小心地关上卧室的门在客厅支开了折叠床,取出了两条毛巾被,一条放在折叠床上,一条放在沙发上,然后自己躺在了小小的折叠床上,指着沙发招呼林芳芳:“孩子有点发烧,已经睡熟了,咱俩在这凑合一下吧。”
“好。”林芳芳躺在了沙发上,盖了一点被,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:“他爸爸呢?值夜班?”
“嗨,去年就离婚了。”赵红梅的语气很平淡。
“啊?咋离婚了?”
“别提了,那狗男人嫌我妈瘫痪了,骂她是拖油瓶,我照顾他妈好几年是一点不提!”
“真不是个东西!”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,所以离婚了。”赵红梅恨恨地说,“爹妈辛苦半辈子才养大孩子,人不孝顺,那连猪狗都不如的。”
“咱妈现在好点了吗?”林芳芳小心翼翼的问。
“也走了……那天我在外面看摊,他找了一帮狐朋狗友在厅里打麻将,我妈胃里不舒服,吐了,又没人盯着帮她翻身……被活活呛死了……”赵红梅的声音像泡了水一样湿淋淋的,从喉咙里浮上来。
林芳芳连忙解释:“姐,对不起,我不是要惹你难过的……”
“没事儿,老太太成天瘫在床上,也不好受。”赵红梅使劲的吸着鼻涕,“人要是该着倒霉吧,事儿都是一块来的。我那段时间还下岗了,护理费太贵,就想着摆摊卖吃的,也没挣到几个钱,前几天摊子还被城管收了,得交不少罚款,现在车还在那边扣着呢……”
她已经把林芳芳当成了亲妹子一样,絮絮叨叨的一直说着,林芳芳垂着眼睛默默地听着。
“唉,这就是命吧,没人能挣得过命。”赵红梅长长的叹出一口气,看着微微亮起的天空,“反正吧,我现在啥都看开了,只要能把越越带大,这辈子的担子就卸下来了……”
林芳芳无言的看着她的侧脸,也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天意弄人
还好那帮人一整天也没再来找事,歌舞厅的午后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。
雷哥趴在门口的小桌上闭目养神,似乎昨晚没睡好,肩膀耸伏,整个人的轮廓像一座小山包。
朱大厨的身影在酒柜旁的小格廊里若隐若现,他正将一瓶瓶杂果罐头码放整齐,同时用余光精心挑选着今晚用哪套果盘。
小雨新买的玻璃唇蜜在化妆间传了一圈,每个人的嘴巴都亮晶晶的,像是擦了层厚猪油。
仙仙把刚领到的热乎工资数了又数,反复整理了好几次,确认无误后才把它们夹入一本存折,锁进妆台。
小恩不知道从哪得来了几样新奇的东西,非要里里外外的炫耀一遍,徐哥说他是“狗肚子装不住二两香油!”。
他笑着展示了一把混色的五彩玻璃丝,两包陈皮梅还有几盘盒装磁带,上面印着同一个头戴鲜花的女歌手甜笑着的倩影。
玻璃丝和陈皮梅立马被女孩们哄抢一空,小恩也不生气,他抠开磁带机的盖子,小心的打开包装盒,放进去一盘,“这是我同学亲戚从香港带回来的!咱大陆还没有呢,好说歹说才借来听两天。”
他按下磁带机的开关,调大音量,痴柔缠绵的音乐缓缓流淌出来。
“如果没有遇见你,我将会是在哪里,日子过得怎么样,人生是否要珍惜……”
小雨嘴巴衔着一股线,两手并用,轮流更换橙色和金色的玻璃丝编织着金鱼,少见的沉默与安静,眨着眼呆呆的听着,珠光眼影浮在眼皮上,闪起一层淡青色的光泽。
夕阳不知不觉间溜进了歌舞厅,又不知不觉地偷偷溜走。
女歌手的中高音又醇又磁、甜如蜜糖,一首首歌连续播放着,大家都听得入迷,嘴里盐津津的陈皮梅也失了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