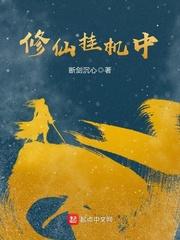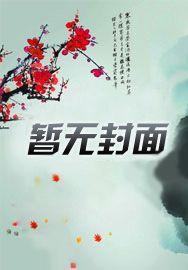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东宫匪我思存全文阅读 > 第40章 筹备明日午宴(第1页)
第40章 筹备明日午宴(第1页)
而在同一时间,任轻欢正在东宫筹备明天的午宴。
在东宫给莫家人设宴接风洗尘,是圣上亲口御准的。太子早早便交代了由她去操持,只道是寻常家宴,太子妃一切从简便可,无需铺张浪费。
事情当然没有那么易办。殿下不想铺张,是怕落人口实,怕别人说太子偏宠外戚、结党营私。
但莫马行毕竟是太子的外祖父,东宫势位得固与莫家的支持有着莫大关系。且老人家镇守边关重地多年,难得能回京一趟,这又是任轻欢次以太子妃的身份款待,说是认亲宴也不为过。于情于理,这洗座宴也得办得好看。
办洗座宴所耗的人力物力极多,东宫领着圣旨设宴,贵和宫自然不敢明着多加阻挠,但自从现了任轻欢的阳奉阴违后,姨母对她也多了几分防范。
掌宫的皇贵妃只要让各宫管事放慢手脚,处处拿足了规矩办事,便够任轻欢头疼的。
姨母是想着她在宫中根基不深,没有操办宴席的经验,借此给她点苦头吃,小小惩戒她的不听话。
任轻欢知道这确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,宴席若办得有声有色,那是应该的。太子妃如果连这点本事也没有,凭什么掌管东宫?之后又如何扶助太子,作后宫之表率?但宴席若有半点不完美之处,不管是多小的小事,也是在外臣面前丢了东宫的脸面,叫太子颜面无光。
太子向来做事极有分寸,他敢把洗座宴交给任轻欢去操办,一来是对她的能力尚算有信心,二来是因为他很清楚东宫尚有个可用之人——李嬷嬷李荷。
李嬷嬷是静德娘娘留下的旧人,在宫中多年,什么样的宴席没经历过?再加上这次款待的莫家人是她的旧主,不用太子特意吩咐,她也必会全力协助任轻欢,做到宾主尽欢的。
但是,出乎李嬷嬷意料之外的是任轻欢的表现。各道菜式的先来后上,该配搭什么酒水、调味料和碗碟用具,她竟如数家珍,打点得清清楚楚,完全不像个新妇。
在琢磨酒菜单子时也一样,莫家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忌口,她都一一打听仔细了,再来敲定菜式。不会只一味的迎合殿下、老将军和老夫人的口味,而忽略了其他人。
在筹备洗座宴的过程中,李嬷嬷渐渐看出了任轻欢的手腕跟能耐,年轻却不失稳重,心思细腻又不会独断专行。
李嬷嬷甚至觉得,任轻欢若要像程贵妃那般独揽掌宫之权,把东宫事务一手抓了,也不是办不到。
但任轻欢嫁入东宫这么多个月了,依然没有半点要插手东宫事务的意思,还是只顾着天天下厨做饭,讨殿下欢心。放任她这个老嬷嬷管着东宫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所有事情。
若说李嬷嬷不好奇任氏有什么打算,那是不可能的。在宫中,能多挣几分权势,就能多几分顺遂。
想逍遥度日,不问世事的人,从一开始就不该入宫。难道任氏以为嫁入东宫就似寻常女子嫁作人妇那般简单吗?任道远的女儿,不可能那么单纯无知吧?
李嬷嬷猜不透任轻欢在想什么,但她确实情愿这太子妃继续游手好闲,虚度光阴。只要她一直不管事,不试图在东宫中建立自己的势力,日后刚玉姑娘入住东宫时,就能更顺利的接管大权。
她听说老将军和老夫人这次回京,带在身边的还有年方十五的小小姐莫刚玉。本来,刚玉姑娘大可随父母留在边疆过年,无需这样长途跋涉的,在严冬中赶回京师。老将军和老夫人既然决定把姑娘带回来了,自然是为了把握这三年一次的回京述职机会,把她送到殿下身边。
如今,一切就要拨乱反正了。
在宫中,权与宠是分不开的,太子妃的位置虽被占去了,但刚玉姑娘只要得到殿下的宠爱,就算没有正妃的头衔也一样能手握正妃的权杖。
日后殿下登基了,谁能成为中宫的女主人,还说不定呢?
李嬷嬷立在东宫侧殿的桌子旁,瞧着任轻欢把小厨房送上来的菜式一一试味,作最后的点评。
「这道百合腰果肉丁虽然香口,但肉丁太多,百合腰果太少,记得提醒御厨留意食材的份量。」任轻欢轻声交代采风。她喝了口清茶冲淡嘴里的咸味,再举筷把桌子中央的清蒸海鱼夹开,检查鱼肉的鲜度:「这鱼蒸得不错,中间还有一点红,鱼肉嫩滑,明天保持这个水准就可以了。」
如今刚玉姑娘回京之事已在宫中传开,不知有多少人睁大了眼睛等着看东宫这边的事态展。任轻欢自然也听到了那些传闻。就算她不想听,也会有太多有心人,想尽办法把话传到她耳边。
但她的态度还是那样沉着冷静,行事不慌不乱的,好像并不为将要生的事感到苦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