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小说网>但为君故刀知道全文阅读 > 第89章(第1页)
第89章(第1页)
“微臣三日前就回来了,刚去拜见过太后。”裴牧之道:“太后她非常关心陛下,陛下可知?”
“知道,知道。表兄,我们还是先进屋吧。”
司马义一面说,一面悄悄挥手让那些宫人全都退下。
两人进入大殿,刚坐下,裴牧之就说道:“陛下,这段时日,微臣不在,不知陛下课业完成的如何?”
“课业啊,”司马义干笑,“我已经完成了,你要不信,可以问太傅,我现在就让田英去传召徐太傅。”
“不必。”
司马义刚要松口气,裴牧之便道:“不用麻烦太傅,微臣可以考校。”
不待司马义找借口塘塞蒙混,裴牧之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,司马义不是回答不出来,便是磕磕绊绊。
裴牧之直皱眉头,司马义年幼登基,没有处理政务的经验,晋王挑选了几位才德兼具的大臣细心教导,司马义资质虽非上乘,但好在勤奋用功,也颇让人欣慰。
可裴牧之离开天都这段时日,司马义不知为何,放纵了起来,每日不是溜鸡摸狗,便是与宫人嘻闹,太傅们拿皇帝没办法,裴太后也劝了几次,司马义当面听过,事后依旧不改,课业全然荒废。
裴牧之越是考校,司马义回答的声音越发低弱,最后,小皇帝干脆破罐子破摔。
“表兄,你别问了,我承认还不行嘛,这些日子,我就是没有好好学习。”
“为何?”裴牧之道:“可是太傅不够尽心尽责。”
“不是,太傅都很好。”
“那就是课业太难、太多?”
裴牧之连着找了好些学习的困难之处,司马义全都一一否决。
“表兄,你别操心了,”司马义双手一挥,赶蚊子似的,“反正我是不想学了。”
裴牧之闻言,声色俱厉,“陛下乃一国之君,如此不思进取,对得起魏国先祖吗?您是天子,天下臣民的表率,理应亲近贤德,远离奸妄谄媚小人,现在却与宫娥宦臣嘻戏胡闹,不务正业,不思悔改,您让魏国上下臣民百姓如何看待?”
司马义被说得灰头土脸,情神羞愧,他对这位长他十岁的表兄很是敬畏,听他如此数落,不免难过,便赌气脱口而出。
“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皇帝的,是你们要我当的,现在却来嫌弃我不合格,即然这样,你们就废了我,另选一个适合的好了。”
殿内安静得可闻落针之声。
“君无戏言,陛下,您的一言一行皆是法令。”裴牧之吐了一口气,“今日之言,微臣没有听见。”
“我是说真的。”司马义道:“朝廷大事我插不了手,我也不感兴趣,你找一个喜欢当皇帝的人来当,反正我是不想干了。”
司马义的确认为当皇帝没意思,每日除了学习就是学习,枯燥乏味,一点乐趣也没有,还不如陈留王时自在。
裴牧之静静看着眼前这位少年天子,他只有十七岁,面容俊秀,眉目中隐然有一派天真。
裴牧之一拂衣摆跪下,“陛下自登基以来,一向勤勉,不曾懈怠,今日却出此之言,微臣不甚惶恐,未能辅佐陛下奋发向上,励精图治,微臣有罪。”
裴牧之将挂在腰带上的印绶取下,双手承上,“陛下,请将赐予臣下的权柄收回。”
司马义吓了一跳,他生母只是一个宫女,偶然得到先帝宠幸,十月怀胎生下他,可这并未改变她悲惨的命远,她不得先帝喜爱,又因生下儿子备受嫉妒,在司马义四岁时死于宫廷倾轧。
如果裴皇后没有收养司马义,他恐怕现在还在某中的角落里,不为人知。
司马义很清楚,他能当上皇帝,依靠的就是裴家,甚至他能在后宫中肆意玩乐,也是因为有裴家存在。
裴牧之要是不干了,别说皇帝,只怕陈留王他也做不成了。
“表兄,你这是干什么,我并不是对你不满,对裴家不满,你快起来。”司马义赶紧去扶裴牧之,可裴牧之动也不动,司马义急了,“都怪田英,他经常在我耳边胡说八道。”
“他说什么?”
“他说我只是一个傀儡,裴家早晚会取而代之!”
魏国的皇宫注定今日不会太平。
执尖披锐的宫廷护卫,来往于楼阁回廊间,间或押出一两个宫人宦者,余者见着越发小心翼翼,不敢交谈。
裴牧之整容端坐,司马义亦坐着,绞衣不语。
田英被拖下去时,他用力拉着司马义的衣摆,尖声道:“陛下,救我,晋王殿下,饶命,奴婢再也不敢了。”
司马义一面偷觑裴牧之神色,一面抽出被抓住的衣角。
甲卫见上面两位没有开口,抓起田英拖向殿外。
田英奋力挣扎,双手乱挥,企图抓住任何可以让他逃生的希望,他大叫,“晋王,陛下,奴婢冤枉,是福康公主,是她,是她教唆奴婢的。”
福康公主司马薇痛恨裴牧之,裴牧之不将她放在眼里,与她和离,使她成为整个天都的笑柄,找到机会,她自然要报复,最省力的法子莫过于挑拨离间。
裴牧之略微思索,便知道是怎么回事,他告诫皇帝,“陛下,您是天子,接近您的人很多,不怀好意的人也不少,陛下要仔细甄别,即便是亲人,也不能全然信任。偏听则暗,兼听则明,望陛下引以为鉴。”
司马义点头,心不在焉。
裴牧之叹气。
临走之前,裴牧裴牧之上了一道奏章,“陛下,北方蛮族进犯边境,微臣想举荐一位能人参与此次作战,望陛下准许。”
“是谁啊?”司马义随口一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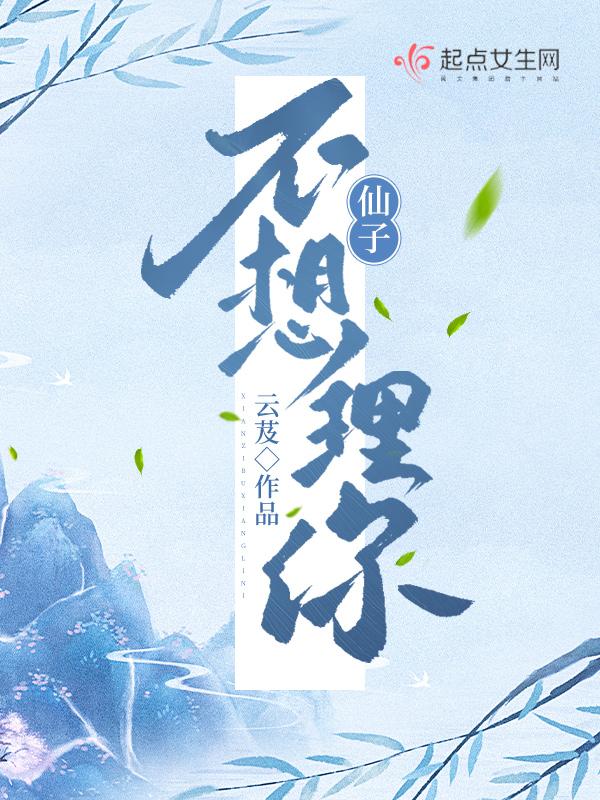
![大佬总勾我撩他[快穿]](/img/14955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