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小说网>盲山盲妻谁写的 > 第10章(第1页)
第10章(第1页)
宇唐脸上一阵潮热,尴尬地低下头。
“其实刚才我好像看见一个人在井口这里徘徊来着,汤老师,你说,会不会是凶手啊?”
“那是你们刑侦队应该解决的问题,不归我管。”汤麦摘了橡胶手套又换上一副新的,重新戴上帽子,“不过你的同事们暂时不会来了,他们抓到了一个人。”
汤麦刚要走却被宇唐的手拦住。
“干什么?”
“汤老师,真的不考虑一下回市局吗?”
“我只是一个门诊法医,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”汤麦看着他真诚的表情,欲言又止,“但是我觉得,我们会再见的。”
7秦妮
这几个老局长的警龄都比较长,用任绘的话来说就是比较迂,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这样不是不好,而是他们的职业决定了行动的突发性,在某些情况之下是不可能按照规矩办事的。
结果因为昨晚的事情,任绘挨了好大一顿批斗,让一个从未有过现场勘察经验的新人独自带队,差点酿成大错。但是念在她抓捕有功,暂时将功补过,等手头上这个案子结束再算账。
从会议室里出来后,联五队还是第一次从这位心气高傲的女博士脸上看到一丝后悔。宇唐的脚踝轻微扭伤,恢复比较慢,现在走起路来像个企鹅,暂时给他划去了所有的户外活动,先安心在队里养伤再说。
但是每人一份得煎饼果子还是按时放在了任绘的桌上,耳朵忙活一上午,肚子也饿了,任绘边吃边说:“对了,昨天宇唐捞上来的证物呢?”
“早就送去证物科了,等化验。”
“你都不知道那群老家伙说了什么,谁还不是从新人时期过来的?咱们是缺人手,但也不用像护犊子一样护着吧。宇唐是彭老师的学生,我也是,老谭你也是,他们瞧不起谁呢?”
“消消气,姑奶奶。”谭享给她桌上放了杯消食的冰水,“局长的意思无非是让你小心点,毕竟是敏感时期,如果宇唐再出事,很难保证外面对市局有什么评价。除非是现在就能抓到凶手。”
“不就是抓个凶手吗?!我非得抓给他们看看!”任绘捏了捏拳头,但一转头她亲生的师弟早已不见踪影,“咦,宇唐呢,今天怎么没看到他人?”
“一大早就在证物科门口等着呢,这小子比你心急多了。”
三楼证据科,包括一间瓜子壳般大小的化验室,人员忙碌,无暇分心。宇唐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,跛着一只脚,“谭队,师姐,你们怎么来了。”
任绘扶着他就近坐下,“坐坐坐,你现在可是老家伙们的‘宝贝疙瘩’,我得重点保护你。怎么样了,结果出来了吗?”
“还没。”
“还要多久?”
“最快还要再等一天。”
“不行!再等一天什么都凉了!老谭,你见多识广,有什么办法吗?”
谭享摇头,“从滨海公园抓来的那个人什么都不肯说,现在也没人去验尸,证物分析结果还要等……唉,难办啊!关键是这个案子现在还不能公开,我问过彭洪椿那边了,他说可以联系到隔壁省市的法医朋友,但是必须征得上面的文件同意。”
“我说你们可真够矫情的!犯了错还可以改正!再说了这案子直接和盲刀案挂钩,请回汤麦主理是必须的!”
“任绘你冷静点,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案子和盲刀案挂钩,一切只是我们的猜测。”谭享使了一个避嫌的眼色将这师姐弟俩拉到一边,“而且汤麦不是因为这件事不想回来,而是……是他个人的原因。”
盲刀案结束后,谭享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去看过汤麦,本以为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会因为这件事情消沉一段时间,但是汤麦很好,拿到停职处分后立刻订了机票,当晚就飞往另一个半球度假,之后整整三个月没有消息。
再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临江路派出所,谭享赶着去给民警送证物化验结果,正巧遇上坐在民事纠纷区的汤麦。
汤麦是一个有严重洁癖的人,但是那一晚见到的人胡子拉碴,衣冠不整,像是刚从一场暴风雨劫难中脱险的难民,浑身上下找不出一处可以辨认身份的标记。谭享还是从执勤民警的电脑记录上看到的名字,汤姓很少见,汤麦就更少了。
民警告诉他汤麦是来报案的,临江公寓楼跳下来一个女孩,年纪不大,没有任何纠纷记录,查到档案还发现她曾经是一名实习警察,说来说去就是很惋惜的意思。据了解,汤麦作为报案人和嫌疑人,居然一点抵触情绪都没有,反而主动要求留下来接受调查。谭享觉得奇怪,于是当晚就留在了派出所和他们瞎聊天,无意中知道了一些事情。
“跳楼身亡的女孩叫做江子非,是汤麦当时主理盲刀案时的助手法医。而且我去现场看过了,确实是自杀身亡。但是,”谭享叹了口气,“那天晚上我一直陪着谭享,他却对我说,是他杀了那个女孩。”
任绘不太相信,“不可能,汤麦的动机是什么?”
“盲刀案法医报告是江子非写的,汤麦一直想找她讨个说法,于是就在临江公寓楼里租了房子便于观察江子非。而就在案发的那天,汤麦喝醉了,正好遇到了出门买东西的江子非,两人因此发生争执,最后……江子非跳楼自杀。”
令人唏嘘。
谭享顿了顿,想要把话题转过来,“我不是没努力过,这几年来每一起案子我都会去邀请他归队,但是始终没有消息。我想他应该不是和我们过不去,而是没办法过自己心里那关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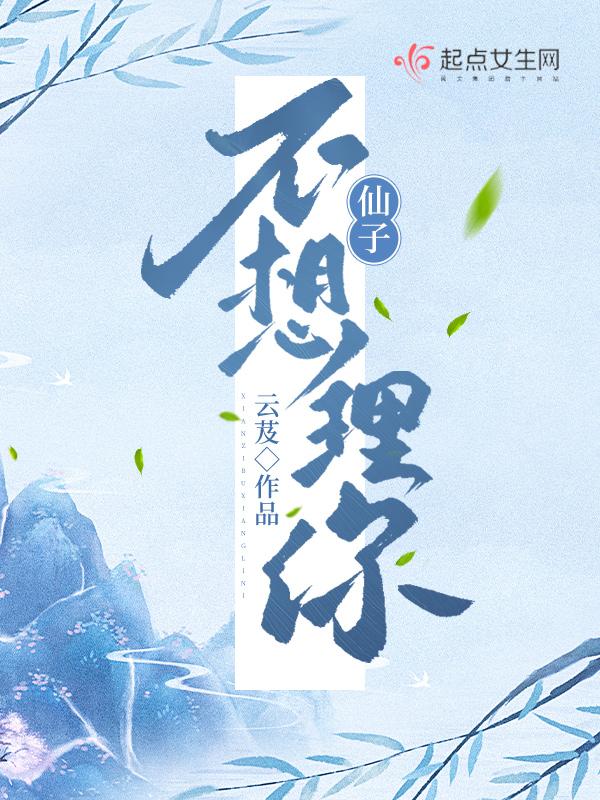
![大佬总勾我撩他[快穿]](/img/14955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