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小说网>智齿咬合处一坨肉经常疼的厉害 > 第54章(第1页)
第54章(第1页)
顾山行木着脸,伸手道:“自己摘吧。”
陈如故面部神经似乎都要抽搐了,他伸出手去摘顾山行手上的戒指,因为是断指所以格外小心翼翼,摘一寸就露出红到发紫发黑的缝线。这戒指一摘,便再也戴不回去了。陈如故摘到一半,被顾山行猛地握住手,人往地上拖,陈如故就摔在那袋凌乱的衣物上,顾山行覆在他身后,沉声说:“拜托,老婆,分手就要有分手的样子好不好。”
“你放开我!”陈如故被他反手拧着,人不由自主的往前倾,全靠他一臂揽着,才不至于跌在地上。
“奥。”顾山行随手从袋子里抽出一条领带,陈如故给他买的,指望他面试时候穿正装用的,一次也没戴过,如今就缠在陈如故的双手手腕上。
“顾山行!”陈如故惊惶地叫他的名字。
顾山行亲吻他耳后,应道:“要叫哥哥。”
“你王八蛋!”陈如故挣的手腕被磨红,顾山行一把抓住他双手,箍在怀里,踢开袋子里散落一地的衣物,在他脖间嘬出红紫淤痕。陈如故错觉鲜血被吸出来,痛感伴随麻意,袭遍全身,他腿软的倒在顾山行怀里,额际竟冒出细密的汗。
顾山行同他亲昵,一边道:“是不是要分手啊老婆,你怎么不说?”
陈如故嘴硬道:“是!”
他越是嘴硬,顾山行吻越炙烈,咬他心脏跳动的位置,像要撕破他胸腔,把心脏掏出来。“你早就是这样的居心了吧?连我行李都收拾好了,就是等我来,落入你的圈套,好让我拎着行李滚是吧?老婆,你真恶毒。”
陈如故诧异,喃喃道:“不是的,我不是的,你不要颠倒黑白。”
“怎么不是,我这一地的行李怎么解释?”顾山行掐着他下巴,要他看地上乱成一团的衣服,陈如故忐忑不安的垂眸,支支吾吾。
“是你…自己经常要拿东西走的。”
顾山行从身后抵上他,压低嗓音问:“我说我要拿了吗?老婆,早对我不耐烦,等着赶我走了是吧,借机跟我发脾气,要跟我分手,不是吗?”
陈如故百口莫辩,在最后一丝理智消失殆尽前,勉强道:“你不听话。”
顾山行彻底抵上他,说:“还要怎么听话?做老婆的奴隶?以后工资都上交,让你管我,嗯?”
陈如故站不稳的朝前栽,顾山行拥着他,发了狠,腔调又冒出丝丝缕缕的无辜,“老婆,不把我的衣柜整理好吗?”
“不…方便。”陈如故断断续续的答。
“好没有礼貌的老婆。”顾山行随手从地上捞了件套头衫,语气强硬,几乎是在下命令,“挂好啊,老婆。”
陈如故赤红着一张脸,瞪他,扬上去的眼尾像在抛钩子,颤栗着去挂衣服。
顾山行在他动作僵硬的挂好衣服后,一记动作连人带衣服都撞向阔大的衣橱。无边的黑暗里,顾山行摸到他潮湿的眼睛,继而往他手里塞了张银行卡,道:“工资卡,以后都你管,别生气了陈如故。”
有一刻,他觉得这种感觉很像成了家,为什么不能弄到一本存折,干脆写陈如故的名字,他会看着上面的数字内容日积月累,如果有一天陈如故问他有多爱他,他就能又俗套又纯粹的掏出存折,说陈如故我爱你有这么多。
几多,像为了生存为了活着而努力的那么多。
就是那么多啊,陈如故。他在衣柜里紧紧圈住陈如故,缝隙的那条光就像银线,他在银线里跟陈如故交融。
“如果有一天,你发现我跟你想象中不一样,”顾山行停顿一下,陈如故呼吸好乱,他叫陈如故乱的更彻底,陈如故被他搅成乱网死结般的毛线,就此解不开了,就像世界上所有无解的命题,他说:“你就只剩接受这一个选项了。”
他戴戒指的那只手拂过陈如故愈渐潮湿的眼睛,说:“一切美好都源自于想象,你能接受美好幻灭吗?陈如故。”
就像他给出的那张银行卡,陈如故再往后就会发现他跟陈如故之间悬殊的工资水平,他捉襟见肘的生活现状,和他无法铺张开的人生。
陈如故抱他后背,摩挲交错的旧疤,笃定道:“你不是我的主观意志,你是太阳你是月亮你是无垠星河你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,你或明或暗或处在明暗交界,这个世界允许你的千变万化,我也一样啊哥哥。我也一样。”
顾山行在他耳边低笑,揶揄他是诗人。
顾山行于是在十二月的化雪天里于衣柜顶撞了一位诗人。
工厂距离陈如故的住址较远,顾山行来回通勤都要四个小时,陈如故主动提出要他在工作的地方租房子。顾山行说不用,有职工宿舍,他周末会回来。
新公司发工资是在月初,顾山行只干了个月底转月还收到一笔工资,尽管不多,他依旧每天在向陈如故报告开支。陈如故仿佛变成了他的记事本。
他发:老婆,烟钱。
陈如故大吃一惊:你抽烟?
顾山行:偶尔…
陈如故:戒烟戒烟戒烟。
顾山行:好的好的好的。
不过一天,他又发:老婆,钱,要买套儿跟油。
陈如故訇然脸红,回说:转了…
顾山行:为什么不多转一点?
陈如故:买那么多要跟别人用吗!
顾山行:消耗品,下的比较快。
陈如故不理他,不想被他远距离撩拨,要等他回来再说他的,要钱花就要钱花,也不用事无巨细的非要讲是用在哪里。
顾山行逢周五回去,俩人简直算得上是小别胜新婚,都这样了,隔天周一在会议桌上遇见彼此的时候俱是一愣,属于是谁也没想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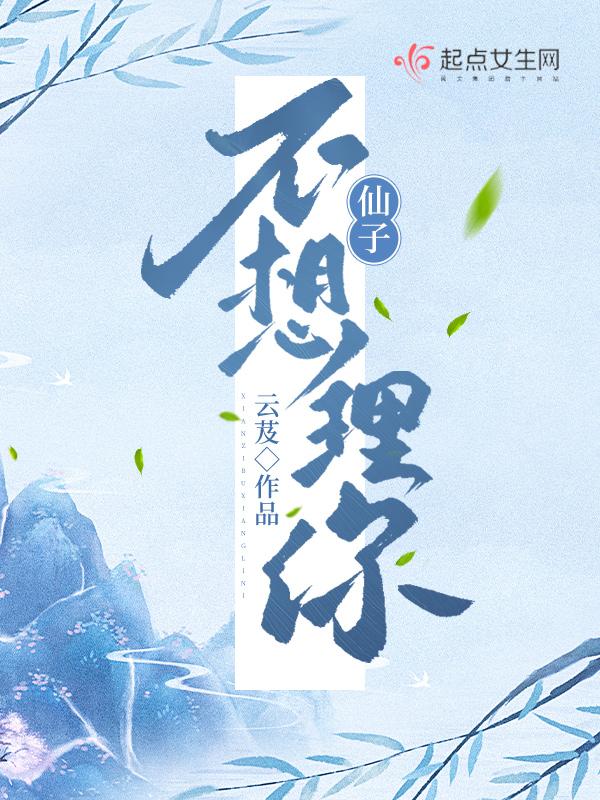
![大佬总勾我撩他[快穿]](/img/14955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