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小说网>智齿咬合处一坨肉经常疼的厉害 > 第47章(第1页)
第47章(第1页)
顾山行抬起眼皮,看他一本正经的模样,低声道:“可是老婆,你都没有挣扎,你拽我手的第一秒我就松开了。”
陈如故愣住,有种被戳穿的窘迫,好像他有多么的口是心非。他于是决定强词夺理道:“没有挣扎,足以说明我对你的宠溺。”
顾山行掀了掀嘴角,觉得他是一只可爱的,对人类有无限包容的,长了满口利齿的毛绒小狗。顾山行一把抱起他向楼上走,在上楼梯的颠簸中对他说:“喜欢也没事,你喜欢什么都没错。”
陈如故埋在他肩膀上,声带好像落在了楼下,赧地什么也说不出。
但总归是因为顾山行右手食指缘故,陈如故从不会去逆着那只手要做的任何事,向来都是默许。
顾山行接到王复群消息时,决定试试左手能否安装机器,这次恰是反过来,他对王复群说这台机器不收费,王复群惊讶地问为什么。顾山行理智道机器组装的周期未知,但他一定会拿去送检以确保合格,他建议王复群这批机器先找别人采,他也不知道他左手能做到什么程度。
王复群这时才知他断了一根指,觉得惋惜,一面感慨世事,他对顾山行说这批机器可能是他最后采购的机器了,因为公司制度变更,他不准备在这家公司待了。奖惩制度变得对员工非常不利,王复群咒骂两句,说之前顾山行来他没经费请顾山行住酒店都够窝囊了,现在制度变得更有针对性了,再待几个月他就准备跳槽。
顾山行没多说什么,只问他那机器还要吗?
王复群说要,只是不准备给这家公司打工了,又不是准备一辈子不打工了。
顾山行说好。
机器要求精密,顾山行左手有时跟不上劲儿,干久了容易抽筋。陈如故不在家还好,在家了就见不得他抽筋,不迭声地让顾山行别弄了,好像顾山行是在吃什么天大的苦。
顾山行干活时候挺不爱让陈如故碰他手的,全是滑腻腻的机油,陈如故心疼完他左手又来心疼他右手,顾山行后来再装机器就给右手戴手套了。秋季愈见转凉,戴手套也不会热,黑色的露指手套,不耽误干活,又能把手指的缝线给遮住。
他是有幅大骨架的,连带着手掌也宽,手指关节粗大,但手指修长,手背青筋蜿蜒,是一双极具力量的手。如今戴上一只手套,便多了分难以言说的意味。
如果他不是在这种天气里穿黑色背心就好了,黑色无比耐脏,虽然洗的也勤,但机油沾在黑色背心上总比白色的好洗,所以他黑色背心就格外的多。
陈如故下班回家就见到他穿黑色背心,鼓胀成型的肌肉随着他扣动扳手拧动螺丝的动作凸起流畅的线条,晚风扬进来,陈如故在或轻或浓重的机油味中走向他,他左手使得很慢,故而专注,没有察觉到陈如故的靠近。
直到陈如故那身裁剪得当的西装顺滑地贴上他后背,鼻尖抵在他脖子,顾山行条件反射地躲避,陈如故双臂环上来,顾山行看到他往上收缩的衣袖露出的精致袖扣和腕表,一同落下的还有陈如故湿漉漉的吻,都印在顾山行后脖子。
“脏。”顾山行抬肩膀躲他,陈如故痴迷地落下亲吻,颇有些不管不顾,手就要往下滑。如果不是顾山行使坏给他摸机油膏,怕这会儿两人就要滚作一团了。
“啊!”陈如故捻捻手指,把机油擦在顾山行胸膛,擦干抹净,黑色背心也看不出来什么。
“手拿下去。”顾山行说他。
“哦,哦。”陈如故迟钝的挪开手,腻歪在他后背说:“哥哥,有料。”
顾山行疑心他只是对黑色背心有什么执念,一面念着他那身昂贵西服毁了要再花多少钱买,一面又觉得单单让二十块钱的地摊货毁掉一身西装太不值,所以就不愿在这时候跟他有什么亲密接触。
“是之前那款氢检标漏配件?”陈如故在顾山行开口撵他之前率先转移了话题,人却还在他身上挂着,晃晃,又想亲。
顾山行用抹布擦干零件,说:“是。”
“噢。”陈如故音拖的有些长,显然心不在焉,闹他耳后,湿湿粘粘地让顾山行错觉像背了只海妖。
“还不下去?”顾山行提醒他,“忘记医生说什么了?”
陈如故大梦初醒,哼一声,先在他耳后重重香一口,才提着公文包朝楼上去的,不忘点菜说:“哥哥,今晚想吃意面。”
从阳台吹来的风让客厅也染上秋意,吃饭功夫陈如故念叨以后天冷了,修理机器不用开那么大的窗,很容易把人吹感冒。
顾山行对此没有表态,他现在仍属于寄人篱下的状态,说好听点是在和陈如故同居,说难听点那便是怎么难堪他都是要受着的。机器只有被陈列的时刻才是崭新洁净的,在未出手前,那种排列组合带来的机油味,会把敞亮的房子渲成库房一样的地方。他很在意,因为这是陈如故休息的地方,而不是他的仓库。
也许他需要一间独立的房间,只在那里装机器。
陈如故看不出他的心事重重,陈如故只看到了他背心下精壮的腱子肉,也许春夜仍在盘旋。
用罢饭后各自回房,卧室光线有些暗,陈如故房门被敲响,他慢吞吞的开门,顾山行进来,换了身松垮的居家服,一双长腿没迈几步就到了飘窗的位置,唤他道:“过来。”
陈如故热切地过去,却在看到他手上拿的锁后脸色苍白,而后转作不健康的潮红。
“我不要。”陈如故拒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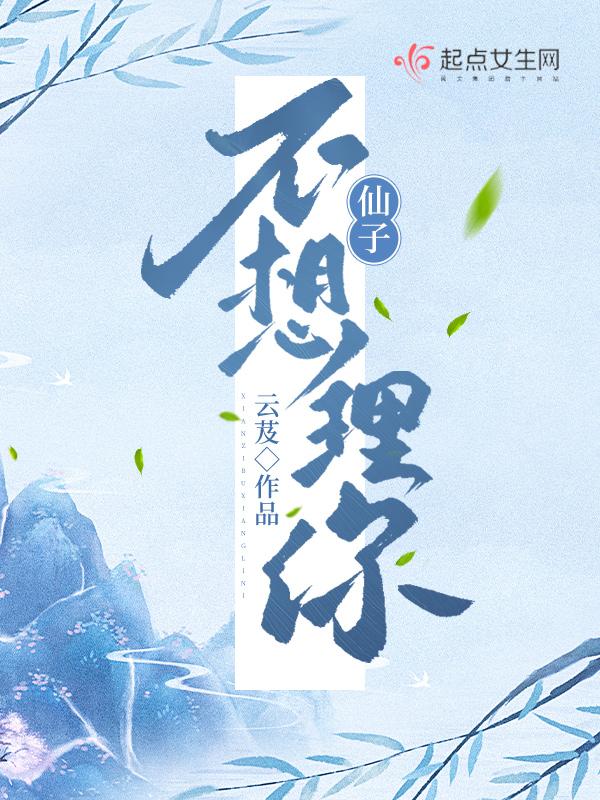
![大佬总勾我撩他[快穿]](/img/14955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