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小说网>饲狼为犬全文免费阅读 > 第4章(第1页)
第4章(第1页)
尉迟枫僵硬在原地不敢动弹,片刻後才听闻耳边响起一声:「跪下。」
尉迟枫还在怔愣之时,白靴坚硬的鞋跟猛地朝着他膝窝一踹,顺势一勾,他被攻势带动着向前踉跄,扑通一下单膝跪在了封庭柳的脚边。
封庭柳转而又踩上他的腿面,仿佛自己脚下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而是给他垫脚的脚踏罢了。
「我还没说你应当做些什麽,你就应下,是否为时过早呢?」
封庭柳的语气染了笑意,他的靴底在尉迟枫腿面上轻点慢碾,像极了磨人的手段。他下巴微扬,看着跪在他面前的尉迟枫红透了脖颈,笑意更盛,接着说道:
「我要的不仅是一个侍卫,更是一条听话的狗。」
狗。
这是一个轻蔑却又暧昧的形容。但尉迟枫却觉得,像封庭柳这样的人,自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臣服他靴下。而他尉迟枫,自然也是那成千上万之一。
尉迟枫一哽,望着那双赤眸,将思绪陷入其中。他恍惚之间,几乎以为自己被封庭柳下了蛊,才会在如此「羞辱」之下毫无怒意,反倒是顺势想要服从。
尉迟枫想不通,却决定顺其本心,扬了扬头,坚定道:
「既已答应,便绝不反悔。」
封庭柳眯起眼眸打量片刻,忽地一笑,「好,好。那从今往後,就由你来伺候我的生活起居。若伺候得好,我便帮你寻回记忆。」
封庭柳将靴底从尉迟枫大腿上移开,悠悠地站起身,一抚衣上褶皱,将手中的烟杆递给了白忠,转头说道:「我虽没有什麽奇怪癖好,但我身边的狗自然也有要学的规矩。随我来,让你看看你曾经的前辈是如何下场。」
尉迟枫站起身,带着疑惑与裤子上那淡淡的脚印跟了上去。
封庭柳带着尉迟枫出了封府宅院,一路上若遇下人,那些下人们皆是又敬又畏地向封庭柳行礼。封庭柳不曾给过他们一个眼神,但自他们的眼神中却能读出对封庭柳的忠心。
反倒是白忠走在後方,会跟下人们和蔼地说上两句话,却也不误脚程,与二人一同出了封府。
三人出封府後向西行去,恰是背对着两个烟囱的方向。他们穿过柳荫大路,来到一处偏僻且阴暗之处,此处有一用岩石垒成的建筑,门口亦有护卫为三人打开了紧闭的大门。
尉迟枫仔细看去,心中一惊,大门後的甬道竟是深邃的台阶,通向油灯幽暗的地室。大门一开,一股混着血腥气的潮湿扑面而来,紧接着便可听闻自地室中传出的阵阵惨叫与哭声。这大门,好似通往地狱一般,有无数恶灵涌动。
可封庭柳却面色不改,率先走进地室。白忠接过守卫递来的油灯,为封庭柳照亮脚下的路。
尉迟枫在心底感叹白忠的细心,亦有心去记,或许下一次要做这些的,正是他自己。
三人走得越深,那些可怖的声音就越清晰。待到石阶走完,尉迟枫才看到了这地室的全貌——这竟是一处关押着无数受刑之人的地牢。
被关在地牢中的人如同恶鬼,身材脱型。他们见封庭柳到来,抑或是崩溃大叫,抑或是辱骂些脏污的话,但这些,似乎都不能影响封庭柳的脚步。
封庭柳带着二人来到一处牢笼前,只见牢中关押着一名身材瘦弱的男人。不,或许他的形态已经难称为人,他的四肢扭曲,牙齿掉了个乾净,嘴巴里空空荡荡,竟是连舌头也无。他只能发出一阵阵沙哑且虚弱的吼声,却连身体都动弹不得。
正当尉迟枫惊讶於眼前所见时,封庭柳忽地问道:「你可知,他犯了什麽错?」
尉迟枫摇了摇头。
「他投靠柳渡城,说亲人被杀,无处可归。我见他年轻力壮,便安排他去照顾院内花草。」封庭柳缓缓说着。
在他说话之时,那牢中的人面露惊恐,不成型的身体一个劲地抖,无法说话的嘴发出「咿咿呀呀」的难听响动。他浑浊的眼睛看向封庭柳,仿佛在看一个怪物。
封庭柳见怪不怪,反而唇角微勾,继续说道:「我本以为忠心的下属,却为钱财,将商队的情报卖给有心之人。商队十人,仅回来重伤二人,你说,如此模样,是否还算罚得轻了?」
牢中的人听了此言,慌张跪下,扭曲地膝行至铁栏前,俯下身向着封庭柳重重地磕了个头。他力气之大,眼见地面上留下了血迹,他却不停。他仿佛想诉说自己的後悔和忠心,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,或是想死个痛快。
但封庭柳连个眼神也没有给那烂泥般的人,反倒是淡漠一眼瞥向了尉迟枫。
「我虽准你留下,但柳渡城也不是什麽人都收。你可听好:
第一,不收对柳渡城无用之人。
第二,不收无法在柳渡城存活之人。
第三,不收任何叛徒。」
叛徒二字重重地回荡在地室牢笼间,激起一片片如同野兽般痛苦的嘶吼。
尉迟枫顿时明白了封庭柳的意思,他郑重地单膝跪在封庭柳面前,入眼所见便是那双白色的长靴。他一手握拳抵在胸口,沉声说道:
「我尉迟枫,绝不会背叛少爷。」
封庭柳俯视着跪在自己脚边的人,看着满是血污的地面弄脏了尉迟枫的裤子,可尉迟枫却纹丝不动。封庭柳忽地笑了。
「你最好是。但你如今脏兮兮模样,实在入不得封府。忠叔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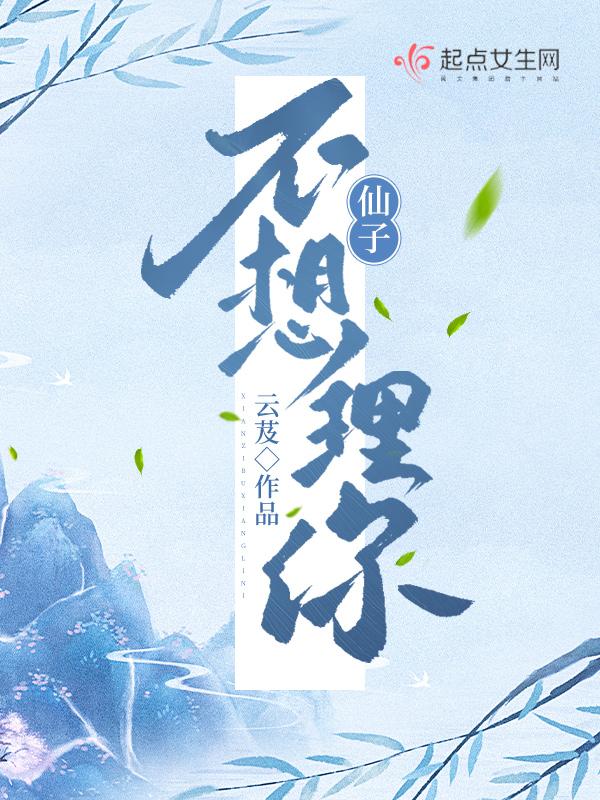
![大佬总勾我撩他[快穿]](/img/14955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