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小说网>烽火念归人香菇酱 > 第81章(第1页)
第81章(第1页)
腊八当天姜培生又拉着婉萍早早起床,想跟她出去看房子。这回婉萍终于忍不住了,甩开姜培生的手,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睡个好觉,让全身的筋骨都睡到舒服为止。
被子卷在身上,婉萍把自己裹成个蚕蛹,只有小半张脸露在外面,紧紧闭着眼睛嘟囔:“你这人太坏了!闲不下来地折腾我!我快被累死了,今天怎么说也不会如你的愿了!”
“没办法,开了荤的老和尚都是这样。”姜培生笑着坐在婉萍的床边,伸手连人带被子地揽进怀里说:“你说我都这么卖力了,这次能怀个孩子吗?”
“我怎么知道?”婉萍的脸烧起来,扭动着身体挣扎两下,却丝毫没有撼动姜培生的怀抱,只能是由他抱着,闷声说:“也许能吧。”
“最好能有,要不然我哪天嘎嘣死了,连个种都没留下。”姜培生说。
“今天腊八节,你乱讲什么混账话!”婉萍一下子睁开眼睛,瞪着姜培生说:“不准说死!”
“好,不说!不说!”姜培生看着婉萍笑:“那换个说法,我是光绪三十四年生人,虚岁今年正好三十有四。我这个年纪,大部分家里少说也有两三个孩子了,可我们现在连一个都没有。我这次回去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,乱七八糟的事情拖一拖,年纪再大些恐怕往后更难有孩子。”
“我又没说不生,该有自然就有了,你不要乱着急。”婉萍垂着眸子,隔了一会儿,声音软糯地问:“如果能怀上,培生,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?”
“我心里喜欢女孩,最好跟你一样,又香又软地招人疼爱。”讲前半句时姜培生还是笑的,但说着他脸色沉了下去:“但眼下这个混账世道,我觉得还是生个皮实抗造的男孩好。万一我回不来,他长大了也能照顾你。若是个女孩子,你们两个人我怎么放心呢?真是死了都没法闭眼。”
“你真是要气死我!”婉萍挣扎着从被子里伸出只手揪住姜培生的耳朵说:“刚同你讲了,不准说死!不准说!过新年不准讲这种晦气话!”
王太太
这一年的年夜饭是陈家到重庆以来吃过最丰盛的一顿,有鱼肉,有鸡肉,还有一大份儿的羊杂汤。它热气腾腾地摆在餐桌正中央,实际却是专门给姜培生一个人准备的,因为陈家人都是不怎么吃羊肉。准备年夜饭时,婉萍问了姜培生想吃什么,他说自己最想念老家的羊杂汤。于是陈彦达第二天天没亮就去早市买来新鲜羊杂,夏青也专门请教了附近开店的厨子。一份苦心好在没白费,姜培生连喝满满两大碗,见他喜欢连着最嫌弃羊膻味儿的婉萍也给自己盛了小半碗。这顿年夜饭难得的和气,期间姜培生和陈彦达还聊起了抗战胜利后对于将来的规划。陈彦达是想带全家回南京,但姜培生却提出来想往北边走,去天津、北平或者石家庄,总之不太愿意再回南京那边。“为什么不回南京?”婉萍问。“首先我能去哪里不是我说了算的,我们内部的人事很复杂,不好同你细讲。如果将来真被安排去南京,对我来说绝非什么好差事。那边官大的人太多,关系盘根错节,是极其难应付的浑水。”姜培生说到他们内部关系时不由地皱皱眉。“东北军、晋绥军、你们中央军,还有新桂系的人,”婉萍说:“从前马太太经常会跟我讲这些。”
这一年的年夜饭是陈家到重庆以来吃过最丰盛的一顿,有鱼肉,有鸡肉,还有一大份儿的羊杂汤。它热气腾腾地摆在餐桌正中央,实际却是专门给姜培生一个人准备的,因为陈家人都是不怎么吃羊肉。
准备年夜饭时,婉萍问了姜培生想吃什么,他说自己最想念老家的羊杂汤。于是陈彦达第二天天没亮就去早市买来新鲜羊杂,夏青也专门请教了附近开店的厨子。一份苦心好在没白费,姜培生连喝满满两大碗,见他喜欢连着最嫌弃羊膻味儿的婉萍也给自己盛了小半碗。
这顿年夜饭难得的和气,期间姜培生和陈彦达还聊起了抗战胜利后对于将来的规划。陈彦达是想带全家回南京,但姜培生却提出来想往北边走,去天津、北平或者石家庄,总之不太愿意再回南京那边。
“为什么不回南京?”婉萍问。
“首先我能去哪里不是我说了算的,我们内部的人事很复杂,不好同你细讲。如果将来真被安排去南京,对我来说绝非什么好差事。那边官大的人太多,关系盘根错节,是极其难应付的浑水。”姜培生说到他们内部关系时不由地皱皱眉。
“东北军、晋绥军、你们中央军,还有新桂系的人,”婉萍说:“从前马太太经常会跟我讲这些。”
“只能说大概是这样,但真要盘算起来,枝枝节节的可就太多了,大小山头数十个。”姜培生啧啧嘴:“就以中央军为例,中央军分成了嫡系,嫡系里的旁系,以及改编的杂牌军。其中嫡系又分成了三大派系,陈的土木系、胡的黄埔生系以及汤的士官系。”
“这样复杂啊!”婉萍忍不住感慨一句,接着问姜培生:“那你们呢?你们属于哪个系?”
“我们不属于他们那三大派系。”被问到了自己,姜培生摇头说:“除开三大派系,我们还有三小派系,第七十四军系统,第五军系统和第五十二军系统。”
听着姜培生说这些,陈彦达的脾气一下子上来了,绷着脸打断:“这个派系那个系统,你们是青帮的在混堂口吗?”
“青帮的堂口哪儿比得上我们的人事复杂,”姜培生无奈地笑了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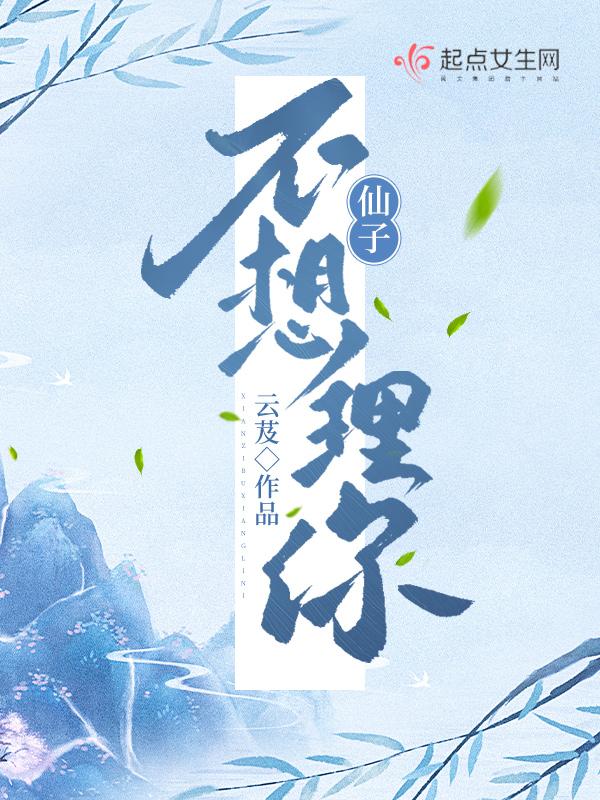
![大佬总勾我撩他[快穿]](/img/14955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