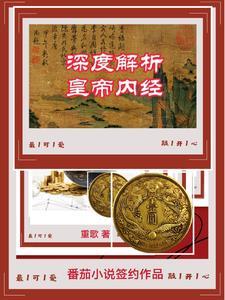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我在七零闹分家 百度 > 毒打(第1页)
毒打(第1页)
“你咋这么毒呢,还要人上农场,上年董二流子进了农场,回来都啥样了,你两只眼是瞎的!”
事后徐振宏不准阮翠莲带徐建红去卫生所。
阮翠莲拗不过老头子,扶起女儿回屋,让她趴在床上。点了煤油灯,火光照映下,阮翠莲轻轻掀开她的衣服,徐建红没了张牙舞爪,声音虚弱细微叫唤,“疼……”
阮翠莲这时候变成了慈母,眼眶干了又湿,小声哄道:“娘轻点,你忍着点。”
徐建红的后背血肉模糊,最严重的地方皮肉已经翻起,身上冰凉。
阮翠莲心针扎一样的疼,心里骂起老头子,这可是亲闺女啊,为了外人,把女儿打成这样,心也太狠了!
她擦干眼泪,走过去使唤柳叶和徐瑾桃,“小叶,你和瑾桃去看看建红,我去给她拿药。”
柳叶最近让闺女洗脑了,徐瑾桃没事就在她娘面前念叨,她奶奶不公平。
柳叶一开始还说自己没生儿子,不让徐瑾桃说。徐瑾桃改变战术,叨叨大伯娘倒是生了儿子,也没见奶奶稀罕大伯娘。阮翠莲自己也不疼大伯和爹,拿小姑姑当个宝。分明她秋后上地,专找咱们的茬嘛!
柳叶有千百句老话下意识地等着自己闺女,可心里隐隐感觉不想反驳。
根深蒂固的老观念和婆婆的话在柳叶心里犹如大树一般,耐不住徐瑾桃时不时来上一句,用铁锹铲上两锨。虽没伤筋动骨,却也砍下了点枝叶。
面对婆婆的吩咐,她第一反应是不愿意。干了一天的活,谁不累啊!刚才还去拉架,做饭。
而且建红做的事情她也觉得过分了,以前觉得小姑子就是娇惯霸道了点,没想到她干这样的事。
阮翠莲见柳叶没动静,张嘴想骂,想到什么又压低声音,饱含威胁:“你是死人呐,听不见我说话?”
徐瑾桃披上衣服,压下要起身的柳叶,头也没抬,“奶奶,你去吧。我去看着姑姑。”
阮翠莲怕晚了孙大夫回家,嘱咐两句急匆匆走了。
徐瑾桃从没进过徐建红的屋子,记忆里原身也没有。
这是徐建红读初中后听公社同学说自己有单独房间后闹绝食要来的。
大冬天的,阮翠莲让大伯和爹给她起的房。
寒冬腊月,大伯和爹在冰冷刺骨的河里捞沙和泥盖房子。她的书桌、床、椅子都是都是爹一点点的打出来的,细心地磨平了棱角,怕他妹妹磕着碰着。
徐建红躺着的这张床,是她爹抽空做了三个月做出来的。
可徐建红是怎么回报的呢?把哥哥对自己的好当作理所当然,为了自己的前程,把侄女推向无尽深渊,惨死山里。
看着徐建红满身伤痕的躺在床上,原身的记忆和情绪迅速席卷而来。徐瑾桃内心一阵恨意与畅快。
她盯着徐建红,恨不得生啖其肉,把徐建红付诸在她身上的加倍还回来!
不着急,我亲爱的小姑姑,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,你慢慢享受。
徐建红听到背后的脚步声,却没有人出声,徐建红疑惑,转头要水喝,就看见徐瑾桃站在床边盯着她,眼神中流露出的恨意与憎恶好似化为实质,射穿她一样。
她惊叫一声,徐瑾桃回过神来,将眼里的情绪掩盖,“姑姑,奶奶让我来看看你,想喝水吗?我给你倒。”
徐建红心有余悸,颤声问: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,那样看着我干嘛?”
徐瑾桃弯腰倒水,笑了,声音轻细,“我看你的伤呢,爷爷真是心狠,怎么能下死手呢,我看着害怕!”
徐建红回想了一下,以为灯光太暗,自己看花眼了,她没力气在追究这点小事,“嗯,快给我倒!”
盖上暖壶盖,徐瑾桃将热气腾腾的水递给她。徐建红一碰就烫的缩了回去。她中气不足,骂人没劲,却依旧改不了盛气凌人的本质,“死丫头,你想烫死我!笨手笨脚的,猪脑子吗?!”
“没有凉水,凉凉再喝吧。”徐瑾桃把搪瓷缸随意放在床头,“还要什么?”
徐建红以为徐瑾桃会想办法把水放凉,没想到她这样做。
以前无论自己说什么,徐瑾桃都乖乖听话,现在看她落难,开始反眼了。果然狗不能喂饱,人不能太好!
徐建红背疼得厉害,蚂蚁咬热锅煎一样,她咬的牙咯吱响,等回来再找这丫头算账!
阮翠莲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,孙大夫正锁门回家。
“老孙,得亏你没走,我女儿受伤了,拿点药。”
孙正平看着阮翠莲一脸不耐烦,今天一天他连口水都没喝上,临了回家还来人。“不能赶早来啊,非等着我回家了才来?”
“孩子让她爹给打了,我这不是没办法吗,你行行好,给我拿吧。”阮翠莲抹眼泪,挡住孙正平。
“三毛钱!拿走!”孙正平开灯配了药,扔在桌上。
“我没带钱,先赊着吧!”阮翠莲拿了药就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