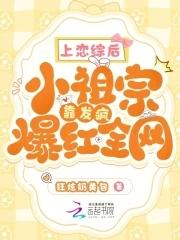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穿到北宋当捕快 > 第24章(第1页)
第24章(第1页)
今年省试比往年早,春寒料峭很折磨人,老苏目送大苏小苏进场後便带上小小苏离开,春闱一考九天,他们只要在考完时再来接人就行。
苏景殊昏昏欲睡,还想回家再补个觉,却感觉回去的路不太对,“爹,是不是拐早了?”
苏洵擡眼,“不早,今天去你王叔父家做客。”
“哪个王叔父?”苏景殊打了个哈欠,他爹人脉太广,姓王的叔父太多,他实在猜不到是哪个王叔父。
苏洵慢吞吞解释道,“你初到京城时在诗会上见过的王介甫王叔父,你王叔父年前进京述职,如今调到京中任三司度支判官,他家雱哥儿和你差不多大,今天先带你去认识认识,之後去国子监也能有个伴儿。”
苏景殊眼睛一亮,王安石啊,晓得晓得,“爹,王叔父家的胖哥儿要和我一起考试吗?”
“你要是觉得这麽想心情好,也可以这麽自欺欺人。”苏洵擡手敲敲儿子的脑袋瓜,“还有,是雱哥儿,不是胖哥儿。”
苏景殊撇嘴,“爹,您进京那麽长时间至今不自卑也是很难得。”
爹和爹不能比,比起来真的能气死儿。
苏洵顿了一下,“人家雱哥儿自幼聪敏,不然你以为你王叔父的《伤仲永》是怎麽写出来的?”
苏景殊不服气,“您儿子也不差,也没见您写《伤和仲》《伤同叔》《伤景殊》啊。”
苏洵淡定反击,“你觉得你爹我在京城是靠什麽扬的名?”
苏景殊:……
那没事了。
第12章
*
王安石家离开封府也不远,不过他们家和苏家不太一样,他们家住的是“公租房”。
京城房价高,作为外地人想在京城买房子难度很大,但是天天住客店也是笔不小的花销,因此大部分人都是租房子住。
朝廷为了解决官员百姓租房的问题,在京城和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来负责公屋的建造、维修、租赁和管理。
京城的公租房大部分都在开封府和国子监附近,开封府附近的租给外地进京的官员,国子监附近的租给进京求学的学子,价格低廉设施完善,身份文书审核通过就能直接入住。
公租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逢年过节减房租,遇见天气灾害减房租,家里太穷减房租,甚至哪天皇帝高兴了心血来潮也会下令减房租。
总而言之,只要有手有脚肯干活,在京城生存下去难度并不大。
文人的圈子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,往大了说全天下的读书人凑在一起都能称兄道弟,往小了说只有志趣相投才会结交。
苏景殊听他爹讲过许多京城读书人的事情,但是至今没弄明白他爹到底有多少个好朋友。
人情世故忒复杂,别说学了,他只看着就脑壳疼。
姜还是老的辣,不服气不行。
今日春闱开场,街上的人比往日少很多,马车穿过州桥回到光化坊没多久,苏洵便让车夫赶车回家。
後面的路途不远,他可以走着去访友。
春闱期间朝廷上上下下都得绷紧神经,但是对掌管财政的三司官员来说,年初这段时间却是难得的清闲。
王介甫如今隶属三司,不趁他清闲多见见面,等过几个月忙起来想见都见不着。
苏景殊脑子里自动把三司变成财务部,表情逐渐震惊,“王叔父在三司,怎麽年前还有时间参加诗会?”
那可是年底的会计啊!
苏洵不以为意,“三司的官员该休息的时候也得休息,总不能调到三司就连旬休也没有了吧?”
苏景殊歪歪脑袋。
好像也是。
父子俩一边走一边聊,不一会儿就走进了公租房的范围。
苏洵苏轼苏辙是地地道道的眉州学子,都没在京城上过学,这些年国子监的变动很大,只靠平时不经意间听到的消息不足以让他放心的把儿子送过去。
就算他不能给儿子兜底,也得给儿子找个伴儿。
苏景殊平时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里和开封府,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,难得跟着亲爹出门心里着实有些紧张,“爹,王叔父年前进京述职,他们家雱哥儿也是第一次去国子监对吧?”
“是第一次,所以才让你们俩先认识认识。”苏洵悠哉悠哉往前走,一边走一边说,“雱哥儿小小年纪便跟你王叔父宦游四方,见多识广行事稳重,你要多和他学学。”
苏景殊笑的露出小白牙,“人家是跟着父亲宦游各地,我父亲出门游学不带我,这可怪不到我身上。”
“小滑头。”苏洵笑骂一句,懒得和他掰扯这些有的没的,“你王叔父是庆历二年的进士,这些年外放做官,深知民间疾苦,他可不喜欢你这样滑头的小孩儿。”
苏景殊清清嗓子,学着他爹的样子模仿道,“介甫兄,这是幼子景殊,昨日刚刚进京~”
苏洵脚下一个趔趄,看着糟心儿子长叹一声,“景哥儿,你我父子非要这样吗?”
言下之意:别逼爹在大庭广衆之下动手。
小小苏立刻化身孝子,“爹,您还能走吗?要不要孩儿扶着您走?”
老苏满意的将手伸过去,父子二人相携前行,好一副父慈子孝的感人画面。
不远处,王安石看着行迹略显诡异的父子俩,嘴角微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