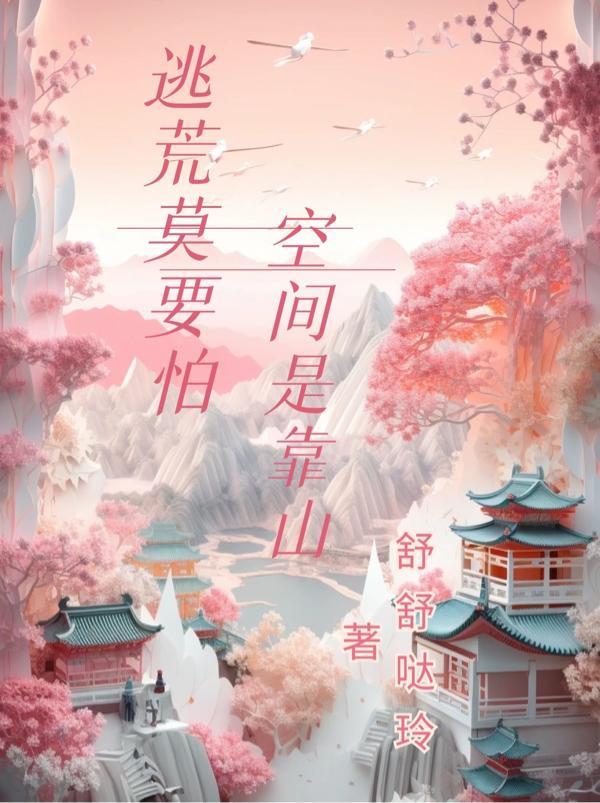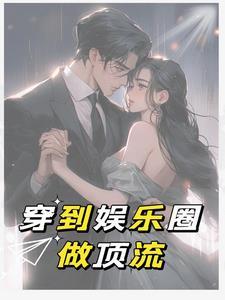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愿得年年 > 第七十三章 圣旨到两章 合一(第1页)
第七十三章 圣旨到两章 合一(第1页)
京城。
赵胜收到消息后,回家后说了这件事,赵父二话不说,带上一群赵家的老哥们便进宫了。
他们刚到宫门口,听到身后有人叫他们,回头一看,好家伙,只见四五个宗室里的老头,手里牵着,怀里抱着,都是自家的孙子和重孙子。
于是,当永嘉帝硬着头皮召见他们时,没等赵父等人开口,这些宗室老头便按着自家孩子给皇帝磕头。
“万岁啊,您看看我家的小孙子,今年三岁,会吃饭、会喝水,肚子饿了还会自己找吃的,聪明着呢。”
“一边去,你家那个除了吃还是吃,哪里像是能做世子的,万岁爷,您还是看看我家孙子吧,这浓眉,这大眼,一看就是随了太祖爷。”
“老五,你的脸皮怎就这么厚呢,那是浓眉吗?那是八字眉,太祖爷是长这样吗?就你家那个丑货,连给我家大金孙提鞋都不配,万岁爷,我家大金孙妥妥的长房嫡孙。”
永嘉帝被吵得脑袋晕晕,烦不胜烦,偏偏这些老头子个个都是他的长辈,而他又惯常是仁孝贤德的明君形象,架子端起来了,想要放下就难了,因此,即使他恨不能马上把这些老东西扫地出门,面上还要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。
好不容易把这些老东西全都打发走了,永嘉帝今天的所有好心情全都没有了,他甚至连乔贵妃那里都不想去了,谁的牌子也没翻,晚上就宿在勤政殿的小偏间里。
可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,次日早朝,都察院十几名御史一起上书,立赵廷晗为世子。
御史们刚刚说完,赵胜便站了出来,他和御史唱起了反调:“启禀圣上,微臣曾经去过梁地,亲眼目睹梁世子的羸弱,虽然现在他病情稳定,但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如何,臣恳请圣上,在宗室中过继子嗣,承继梁世子的血脉。”
此话一出,满朝默然。
宗室争先恐后要给赵廷晗过继儿子的事,早已满朝皆闻。
并非是宫里传出来的消息,而是现在宗室营里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这件事,这早已不是秘密,估计不出三日,整个京城就没有不知道的了。
都察院的四大金刚,随着靳御史的英年早废,如今只有硕果仅存的三大金刚了。
都察院人才济济,想要跻身四大金刚的御史大有人在。
所以现在根本不用孙钱石这三位御史大展雄风,赵胜话音刚落,便有七八名御史站出来,引经据典,将赵胜驳斥得恨不能挖个洞藏起来。
这些御史的辩论主题只有一个,那便是梁世子年方十九,风华正茂,即使他的身体欠佳,可也不能代表他不能开枝散叶,御史们列举出古今多位体弱却有子传宗的例子,上至王侯将相,下至贩夫走卒,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最终,御史们大获全胜。
刚刚下朝,一群宗室老头便又递牌子进宫,永嘉帝没有召见,这些老头便抱着自家大孙儿,在宫门外面候着,这一候便是整整一天。
已过中秋,京城的秋风已经有了凉意,这些人老的老小的小,当天晚上便有几个病倒的。
如果是太上皇那种不管不顾的也就罢了,他们只能自认倒霉,可是永嘉帝不是太上皇,永嘉帝是明君啊!
面对明君,当然不能打破牙齿和血吞,把苦楚藏起来,那就是对明君的不敬。
次日一早,永嘉帝还没去上早朝便知道了这件事,无奈之下,只好派了太医出诊,又给每家送去了药材,
而今天的早朝,辩论的主题仍然围绕梁世子赵廷晗,只是甲乙双方,已经从让赵廷晗自己生儿子和从宗室过继,变成了赵廷晗自己生儿子和从亲弟弟赵廷暄那里过继了。
又是一番唇枪舌剑,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,而永嘉帝再一次真实地感受到,此时此刻,自己就是一只被架在火上烤的羊。
因为无论是让赵廷晗自己生儿子,还是让赵廷暄生儿子,或者是从宗室过继儿子,这些都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赵廷晗继承王位!
这些事,都是赵廷晗继承王位之后的事。
第三天,仍然如是,好在后面的两天不是大朝会和朔望朝,参加辩论的官员相对减少,否则永嘉帝可能已经被他们吵到爆头了。
即便如此,永嘉帝依然不得安宁,锦衣卫送来的消息,如今京城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件事,且,乡试刚过,很多学子还没有离开京城,考上举人,准备明年参加春闱的,此时都在忙着温习功课,可是这毕竟只是一小部分,更多的是没有考上的,他们现在都很闲,且,内心极度不平衡,他们不觉得考不上举人是自己技不如人,而是认定这是怀才不遇,他们不是没有考好,而是阅卷的考官眼光有问题,错过了他们这些千里马。
受了这么大的委屈,当然要发泄了。
因此,大街小巷,酒楼茶馆,随处可见直抒胸臆的读书人。
锦衣卫暗中抄录了这些读书人的言论,送到永嘉帝面前,永嘉帝气得想要吐血。
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,十几名滞留京城的外地书生被抓进了诏狱。
“杨兄,你可听说李兄和张兄的事了?”一名书生找到杨胜秋。
杨胜秋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解元,已有几位朝中大臣向他抛出橄榄枝,但是杨胜秋全都婉拒了,他的目光看向更高处。
他摇摇头:“这几日我都在温书,已有多日未曾见过李兄和张兄了,他们出了何事?”
书生四下看看,压低声音:“昨天晚上,他们被锦衣卫带走了。”
杨胜秋倒吸一口凉气:“锦衣卫?他们近日可是言行有误?”
书生叹了口气:“你一定也知道,张兄家境殷实,以前也时常邀请大家游园赴宴,这次亦是,他包下城东的金菊园,办了一场赏菊诗会,他和李兄素来交好,他办诗会,李兄定然跑前跑后帮他操持,可惜我才疏学浅,没能得到请帖,杨兄乃今试的解元,想来是收到请帖了吧?”
杨胜秋:“我确实收到一张请帖,然学业为重,我推拒了。”
书生很是遗憾,也不知道是遗憾杨胜秋收到帖子却没有去,还是遗憾杨胜秋没有跟着张兄李兄一起住进诏狱。
杨胜秋问道:“可是那诗会上出了问题?”
书生低声说道:“那场诗会中出了几首好诗,不到一日便传遍京城,这一次被锦衣卫抓走的,除了张兄和李兄这两位诗会的组织人,便是写那几首诗的人了。”
杨胜秋懂了,定然是这些诗出了问题,他暗中松了口气,来京之前,方大儒便叮嘱过他,不要参加那些书生们办的诗会文会,现在看来果然如此。
京城藏龙卧虎,但也危机重重,他想在京城站稳脚跟,必须步步为营。
然而如杨胜秋这样想的年轻人只在少数,更多的是满腔热血,愤世疾俗。
其中被抓的那位姓张的书生,素来有小孟尝之称,他在书生之中人缘极好,有很多手头拮据的书生都曾得到过他的资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