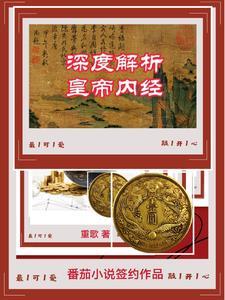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封神殷商妖妃太贤良了吧 > 第30章(第1页)
第30章(第1页)
既白理直气壮:“不会有任何错漏的,师叔的灵发会一直保护着我的。”
九日在她的自信前说服自己相信教主,将自己小心暂时剥离。
过了许久,外面呼啸而来的甲胄碰撞声如同沙石呼啦呼啦作响,天色逐渐的明亮起来,皎洁的月潋滟着光辉。
一狐貍一兔子久久无言后憋出来一句:“你知道要祈福献祭舞蹈的吧?你会吗?”
既白皱眉:“这不是自然而然就会的事吗?”
她的师叔是圣人。
圣人是什么意思,扭转乾坤,超出六道。
她用通天师叔的法器让自己顺利成为大祭司,当然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发生。
大典开始之时,天色刚刚擦亮。
太阳还未曾升起,月满未央,模模糊糊的的光亮和残留着的寒冷让呼出的每一口喘息都泛白。
大军银盔铁甲,百官严阵以待。
一步步繁杂的阶梯连接着巨大无比的高台,此刻中央烈火熊熊,映衬着每一个人的面容都带着流动的火光。
殷寿并没有穿着他那象征着王子身份的冠冕,而是如同在战场上纵横捭阖一般,穿着只属于他的黄金甲,猩红的披风摇曳在风中,如同一道蜿蜒的血海。
与他站在同一位置,还从站位上隐隐约约压过殷寿一头的大王子殷启被衬的黯然失色,如同其他陪衬一般引不起任何的注意。
但今时今日,殷启却已经不在在意这些,能够在这种场合让自己人压住殷寿已经让他喜不胜收,想不起其他事,哪里还能想的到其实他和既白并没有任何交情,甚至既白和他儿子之间“两情相悦”的名分也并未确定。
不过自从有西伯侯夫人连续生育,对自己领地无能为力,只能连并西岐后,所有男人都明白,拴住一个女人的法子,就是让她生孩子。
拴住女人所属领地、权力的办法,就是让她一直生孩子,永远不停地生孩子。
既白,又有什么例外?
女人,总是这样,虽然身强体壮,喜欢在战场上、在朝堂上和男子争抢,但只要这一个致命的弱点在,那就只能被拿捏。
殷启在脑海里浮想联翩,幻想若是既白和殷郊婚后生下他的孩子,该怎么称呼殷郊?
若是他有了新的儿子,殷郊也就无用了,那他这个慈父又该如何处置?
鸟雀飞过,一声声的“呃呃”撕裂了寒风中萧索的空气,更化解了其他人紧绷到极致的神经
殷启仰起头得意一笑,对着神色肃穆的殷寿说道:“玄鸟出现,看来大祭司万分得以偏爱,真是让孤都不免新生嫉妒之心啊。”
“不过人和人的差距,从出生的那一刻时就已经注定,往后须臾数年的努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蜉蝣撼树罢了。”
“这是怎么嫉妒也嫉妒不来的。”他挑衅的望着自己的弟弟,还顺道看了一眼伯邑考发白的脸色。
“想必,二弟也应当十分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身后落了半个身位的殷郊再是如何迟钝也听出不对,但他实在不知晓该要如何制止父亲,只得在身后面露恳求朝着叔父无言的赔罪。
姬发脾气一点就着,他的站位逊色于皇孙殷郊,和殷寿这位主帅的亲兵统领伯邑考,却依然以百夫长和西岐世子的身份占据更多高官贵族才有的位置,听得那叫一个清清楚楚。
他本来就讨厌沉迷酒色的殷启,更加尊敬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二王子,如今再加上既白——
姬发不愿意既白成为这种人嘴里炫耀的恭敬。
“昔年大贤曾经禅让王位,殷商先祖只是夏朝臣民,难道大王子也觉得先贤有错,殷商先祖有错?”他少年在这天光未亮的夜里冷冷的开口,脸上是未有任何修饰的不服和桀骜。
话题中心内从未开口一言的殷寿此刻在一瞬间面露欣赏。
剎那时,风声鹤立,战鼓齐鸣,熊熊火焰好似将苍穹染红。
两兄弟在只有他们能够听到的距离内,平静无波的殷寿这才开口笑言:“大哥,对看不上眼的猎物只需要一击即中,而对猎人上蹿下跳极尽试探,那正说明,内心空虚啊。”
“人的成果在出生时就已经注定的话,那大哥更应该思虑自己究竟是做了什么,才会让你面对自己的手下败将心虚的很。”
殷启被一句话激怒的怒不可遏,当即就忘了现在是什么地方只想着要好好教训殷寿,于是一把拳头没有任何思考直勾勾的便冲着这次战场的主帅而去。
殷寿眼底全是讽刺,他连制止都没有制止,只冷眼看着他沉迷享乐的兄长在他稍稍躲避后收不住力气,一下子颓败的倒在地上。
暗骂一声无用。
这样的人做储君,除了比他早早出生一些年岁外又有什么胜过他的地方?
他又如何能够心服口服?
一群铁杆太子党蜂拥而至搀扶起殷启,但这时殷寿已经无暇关注手下败将的情况,视线内只笼罩在那模糊的身影中。
初见时,殷寿只觉得这位大祭司是个美人。
一张脸如同细细描绘的牡丹花,美人雪一般的肌肤镀着一层浅淡的釉光,娇嫩的如同二月枝头新冒芽的新柳。
柔弱、无辜、适合被捧在掌心,揉在怀中,即使她的话语伶牙俐齿给了殷寿几分印象,也未曾觉得她有任何特别之处。
直到如今。
皎洁的月光还未曾落下,崭新的太阳已经从东边逐渐升起。
她穿着诡异纹路遍布的玄色礼服,面上带着一面如同鸟脸尖锐,羽毛林立,额间又有红色小点,仿佛下一瞬这张面具之下便会有惊诧的鸣叫之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