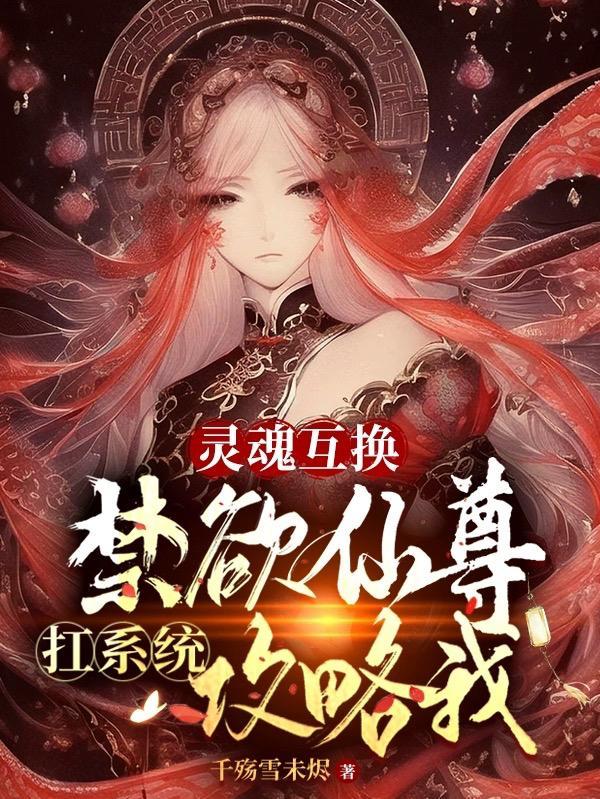读小说网>玉娇龙续集春雪瓶txt免费阅读 > 第25节(第2页)
第25节(第2页)
毕竟烫伤比冻伤还要厉害些。
他摩挲了一下那瓶子,眼角余光忽然瞧见一点光亮了起来,他抬眼一看,是偏殿。
这个时辰才回来,太后用起人来果然是不客气。
他收回目光继续去看那折子,而后提起朱砂笔将天下之治这个考题给圈了出来。
春闱是他的机会,只靠世家之间互相抗衡是不够的,他要扶植寒门,只有寒门出身的人,才能明白百姓的难处,才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做事,为皇帝尽忠。
希望今年能有更多身家清白的天子门生吧。
他叹了口气,抬手将折子合上丢在了矮柜上,侧头又看了一眼窗外,刚才亮起来的那点烛火却已经灭了,整个偏殿安静得像是没有人住一样。
他怔了怔,脸黑了。
第二天身边伺候的换了人,殷稷扫了一眼那张陌生的脸,目光落在蔡添喜身上:“怎么,她得罪你了?”
语气淡淡的,可听得蔡添喜一激灵,他连忙躬身:“奴才岂敢和谢蕴姑娘生气,是她给奴才递了话,说是今年新进了后妃,宫里的事务比往年更繁杂,她分身乏术,又怕怠慢了皇上,这才让奴才提了个人上来暂时伺候着。”
那小宫女一见殷稷对自己不满,已经十分慌乱地跪下了,有了香穗的前车之鉴,她被吓得不轻,低着头动都不敢动。
殷稷挥挥手将人撵了下去,脸上却带了几分嘲弄,真这么忙还是寻个借口不想见他?
他抬脚出了乾元宫,见蔡添喜要跟上来,不轻不重的点了他一句:“对你而言,主子重要,还是差事重要?”
蔡添喜大约是听明白了,伺候他下了朝就唤了德春来伺候,自己匆匆走了。
殷稷抬头看了一眼,随即便将注意力放在了奏折上。
这一日政务少,他下午便回了乾元宫,蔡添喜殷勤地问他可要宣后妃来伺候,他摆了摆手,捡起本书打发时间,眼看着日头慢慢落下来,偏殿里仍旧十分安静。
手里的书一页页翻过去,灯烛也换过了一茬,乾元宫里仍旧没人回来。
殷稷皱眉合上书,目光落在蔡添喜身上,对方被看得不明所以,语气十分困惑:“皇上?”
殷稷又将目光收了回去,更漏一点点浮起来,三更悄然划过,蔡添喜小声开口:“皇上,该歇着了。”
歇着?
殷稷将书丢在矮几上,动作不大,可夜深人静的,这动静仍旧唬得蔡添喜心里一跳,心虚地低下了头。
然而殷稷又什么都没说,只目光沉沉地看着他。
蔡添喜没办法再装傻,只能讪讪开口:“皇上,奴才今天去了长信宫,可谢蕴姑娘的确忙得厉害……”
话还没说完,殷稷就打断了他,语气十分不耐:“谁让你去找她了?朕这乾元宫难道缺人伺候吗?”
他一甩袖进了内殿,蔡添喜松了口气,却又哭笑不得。
是,皇帝一个字也没说,可早晨那句话分明就是想让他转告谢蕴,差事再重要,也别忘了自己主子。
现在倒好,成了他多管闲事了。
可他是个奴才,不敢和自家主子计较,只能摇了摇头,抬脚跟进内殿想伺候殷稷歇着,可刚进门就被撵了出来。
殷稷打小生活在萧家,私务自己处理得十分妥帖,蔡添喜被撵出去也不是一回两回了,他乐得清闲,很快便回了自己的院子。
等乾元宫彻底安静下来,谢蕴才疲惫地回了乾元宫,第二天天还没亮便又去了长信宫。
太后大约还是恼怒殷稷没有把掌宫的事顺势交给惠嫔的,很多该长信宫出面的事,她都丢给了谢蕴,再加上今年多了几位主子,差事像座小山一样砸下来,压得她颇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加上前段时间被关得太久,精神很有些不好,短短几天功夫,谢蕴便累得脑袋隐隐作疼。
可她生来性子要强,便是当真不舒服也只是咬牙忍着,她总不能除了床上,真的没了旁的用处。
外头喧闹起来,来送早饭的长信宫女说是后妃们来给太后请安了,连多病的良嫔都在。